二酉山房歌
君不见昆崙高高阆风出其上,下视扶桑弱水相去几千丈。
傍开四百四十门,日月东西互相望。传闻大酉小酉双名山,乃在昆崙阆风二岳之中间。
帝遣藏书号群玉,金庭石室森钩连。白虹璀粲映缃帙,朱霞错落垂琅函。
自从轩辕来,窅绝殊人寰。灵威丈人过,缩足不敢前。
成周穆满驱八骏,蹑电乘风到灵境。岚深谷峭黯莫留,却携王母升蓬丘。
祖龙炎威扫六合,秦人留书闭空峡。至今玉洞开桃花,仙源可望不可涉。
坑灰未冷汉社兴,大儿中垒小子云。藜然天禄下真宰,烂漫七略罗天人。
阮家居士重蒐录,蠹简纵横委胸腹。湘东再火一不留,七万瑶华烬荒簏。
聚书崛起开皇朝,缥囊璚笈摩丹霄。累累三十七万卷,嘉则之殿高岧峣。
诸儒雠校汰冗杂,正本亦止三万饶。开元八万最奇绝,往往玄珠出岩穴。
宋时群主竞好文,一日三诏何缤纷。后来马郑诸子出,摩娑论列亦已勤。
好武遍中华,马上为生涯。诗书匪故习,文具徒矜誇。
鸿荒重剖大明域,九曜含辉聚东壁。天开地辟恢雄风,雾涌潢流映朝日。
吾乡文宪达最先,高文大册挥如椽。青萝读书四十载,钻研法藏窥重玄。
云间子渊嗜缀辑,断简残萤映墙壁。成都用修雅好奇,索摸科斗成嗔痴。
南阳陈卿负综博,一生惟折五鹿角。北海冯君推殚精,歌谣委屑烦经营。
突兀琅琊起文苑,力挽颓风究坟典。尔雅楼中四万轴,金石斋头五千卷。
须弥磅礴宛委深,吐纳宇宙横古今。张王陆沉驱左席,何因物色来兰阴。
兰阴胡生负书癖,早逐刘郎卧岩石。髫年已绝轩冕好,壮岁偏耽穷鬼力。
北走燕台东走吴,金陵闽越穷江湖。僦居寄庑录馀烬,负薪织履偿追逋。
陆则惠施水米芾,昏黑忘眠昼忘食。乍可休粮饿途路,讵肯空囊返乡国。
二十四庋罗山房,二千四万堆琳琅。黔娄妻子困欲死,君山箧笥富可量。
上距羲农下昭代,触手牙签宛相待。圣神贤哲穷吁谟,帝伯皇王罄元会。
一榻一几横疏寮,一琴一研祛烦嚣。焚香独拥四部坐,南面王乐宁堪骄。
黎生八分称好手,夜宿山斋笑如斗。纵观丘索盈前除,大叫狂呼题二酉。
琅琊作记当代传,姓名已睹琬琰悬。触目伤心故交尽,却寻司马来新安。
司马心胸旷千古,夙昔图书探天府。三坟二雅勤雕锼,一笈五车劳缀补。
太函峨峨云际开,恍入东观窥兰台。众中誇我好玄者,撑肠拄腹谈天才。
寂寞萤窗守残雪,揽镜苍茫见华发。声华岂必专穷愁,著述总知成灭裂。
侧身六合中自疑,异代乾坤未堪说。感公国士知,肝肠为公竭。
幔亭十日饮,驱车复成别。回看二酉山,崚嶒渺天末。
昆崙阆风定何处,弱水扶桑杳难越。底似从公居太函,副墨煌煌恣翻阅。
君不见太函五城十二楼,金银城阙天尽头。陶公八翼不得上,梯仙岂合凡人留。
孤帆且返越江涘,俛仰竹素聊优游。异时四部读已尽,玄关或许停苍虬。
君不见兰阴下,瀫水流,轮囷古木枝相缪。瓮牖绳枢闭荒径,荜门蓬巷悬清秋。
夜夜红光烛星斗,兀兀陈编柳生肘,短铗长檠竟何有。
醯鸡瓮里真自笑,蠹鱼架上安足友。竺乾本来一物无,柱下青牛亦西走。
函中领取五千言,赤脚流沙寻二酉。
(1551—1602)明金华府兰溪人,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更号石羊生。万历间举人,久不第。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记诵淹博,多所撰著。曾携诗谒王世贞,为世贞激赏。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诗薮》。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谁不道富贵千金夜,我翻做凄凉三月节。怀故人万里离别,负东君一番艳冶。
【梁州】相思鬼皮肤里打劫,睡魔神眼睫上盘踅。可正是多情自作风流孽。
锦鸳翎活扯,丹凤颈生扌绝;并头花揉碎,合欢树攀折。升仙桥闪却车︷,武陵
溪下桩撅。声沉佩玉玎,尘满钗金蹀躞,香残褥锦重叠。想者,觑者。冷清清
空落下读书舍,越间阔,越情热。你便是一寸肝肠一寸铁,也害得痴呆。
【余音】本待向楚王宫半缄剩雨残云赦,怎下的海神庙告一道追魂索命牒。
不是我怪胆儿年来太薄劣,将枕边厢话儿说,把被窝儿里赚啜,都写做殷勤问安
贴。 夏闺怨
燕泥沾白象床,麝尘暗冰蚕褥,萤灯照青琐窗,蛛网络碧纱橱。一弄儿萧疏,
镜里人何处,樽前谁是主?凄凉煞锦水鸳鸯,寂寞了雕笼鹦鹉。
【梁州】下几点梅子雨间一行情泪,荡几阵藕花凤助一口长吁。几般儿堪写
入伤心灵。金步摇花残蹀躞,玉搔头线脱珍珠;蔷薇露羞和腻粉,兰蕊膏倦揽琼
酥。上妆楼一步一个趑趄,指长亭一望一个糊突。紫香囊徒效殷勤,白纨扇空题
诗句,锦回文枉费工夫。咱两处旷夫,怨女。料应来昏配了姻缘薄,多间别,少
完聚。抵多少夫在萧关妾在吴,凤只鸾孤。
【骂玉郎】也是我孜孜的撺断他学干禄,嗟行事,悔当初,多情却被列情误。
唤不应离恨天,填不满忧怨海,赶不上相思路。
【感皇恩】这些时鬼病揶揄,更那堪睡魔追逐。软兀刺弱身躯,颠不刺乔证
候,干支刺瘦肌肤。无半点欢娱分福,纯一味鳏寡孤独。叮咛话总虚词,断肠诗
成故纸,平安信似休书。
【采茶歌】他指望八仙图,我贪爱七香车,犹恐怕黄金窑变了汉相如。蓍草
占来爻反覆,卦线儿磨得字模糊。
【尾声】虽忘了并头莲空房独守心常苦,也合想连理枝嫩绿成阴叶未枯。手
抵着牙儿自犹豫,几时得ゐ惶业足。多管是凄凉限促,不由人蘸绿亭前放声儿哭。 客中奇遇寄情代友作
风月长存一寸心,雨云又作三春梦;青鸟不传千里信,落花空恨五更风。想
当日旅馆相逢,取次间谐鸾凤。实心儿担怕恐,瞒不过纱窗下半篝残夜孤灯,喜
的是罗帕上数点芳春嫩红。
【梁州】碜可可言誓海深如渤,热刺刺设盟山高似崆峒。经几番柳惊花颤
娇团弄。金解麝兰馥馥,宝钗横雅髻髻;粉汗湿耨声悄悄,罗袜翘底样弓弓。
实承望效鸳鸯百岁和同,不提防赋骊驹两字西东。又不比卓王孙听琴声慕相如发
忠,张延赏招赘时叹韦皋命穷,贾公闾偷香处知韩寿情浓。自非,懵懂。没来由
信流莺唤出桃源洞,越懊恼越疼痛。回首关河几万重,无计相从。
【尾声】全不想上阳关登云路紫骝蹀躞催丝,长则待谐姻眷开玳宴翠袖殷
勤捧玉钟。寄与那闲打牙的相知幕讥讽,少不的凄凉卷终。风流命通,恁时节花
烛兰房慢慢的宠。 赠教坊殊丽
眼舒随意花,髻插忘忧草,手拈红麝尾,口里紫檀槽。一撮儿娇娆,常记得
阳台梦曾奚落,武陵溪犹撞着。人都道绮罗乡再长个卿卿,我猜做风流地重生个
小小。
【梁州】说窈窕端然窈窕,待苗要不甚苗备。向樽前彻胆儿包藏着俏。肌雪
莹匀匀粉腻,脸霞酣淡淡红潮。豆{艹寇}小半含玉蕊,丁香嫩一点春娇。舞衣轻
燕体飘飘,歌喉细莺语。缕金环嵌八颗珠,交股钗袅双头凤翘,凌波袜荡
六幅鲛绡。老陶,见了。少不得剖肝肠再写段《风光好》,年纪儿正芳妙。纵舍
千金度一宵,没福也难销。
【尾声】烛荧煌香铺张个夜月芙容幄,锦缠联金络索搭苫个春风翡翠巢。
我是鉴乐的酸丁最公道。遮莫将丹青画描,词章品藻,兀的般解语花生香玉世间
少。 赠素云
轻柔缟淡妆,缥渺瑶华动。分开山雾紫,冲破海霞红。溶溶,聚散如春
梦,飘零似转蓬。离恨开几弄儿昏迷,风流地一遭儿乱拥。
【梁州】可怎么黄鹤楼头不遇,常则是青山画里相逢。淡丰姿沮得个人知重。
笼夜月梨花庭院,弄春阴杨柳帘栊。讴清歌依依金屋,舞霓裳队队瑶空。又不肯
化甘霖相趁游龙,常则待带斜阳常背征鸿。没乱煞老梁公归兴凄凄,吸留煞
忄刍谢安芳心冗冗,奚落煞闷襄王佳会匆匆。好风,怪风。绕天涯几度相迎送。
不落锦胡洞。多在巫山十二峰,无影无踪。
【尾声】一任他漫天巧结银河冻,半霎儿满地平铺素剪绒,则落得高卧先生
恣抟弄。向瀛洲海东,入蓬莱洞中,煞强似太岳祠中受恩宠。 嘲素梅
休言白玉堂,怎知黄金鼎?难栽玛瑙坡,宜插水晶瓶。索笑为生,冷淡偎村
径,朝昏傍驿亭。常则是采薪夫觅觅寻寻,那里取惜花客潜潜等等。
【梁州】琴谱内又不将宫商剔拨,角声中常则是趁钟鼓悲鸣。我将他根脚儿
从头省。大庚岭多年的魑魅,罗浮山旧日的妖精;东阁外移来的异种,西湖上流
出的残英。虚提着玉洁冰清,空落得雪虐霜陵。孟浩然见了呵了吟鞭,赵光普
觑了呵罢了谏诤,杨补之画了呵唬了魂灵。试听,他本情。未成实先有酸心病,
可知道楚大夫厮奚幸。万吉《离骚》不入名,枉自飘零。
【尾声】打不动裁冰剪雪林和靖,冲不过击玉敲金宋广平,纵泄漏春光也不
干净。趁风清月明,恐天寒地冷,则不如收拾横斜水边影。 赠明时秀
星靥靥花钿簇翠圆,黑вв云髻盘鸦小;金闪闪袜钩舒凤嘴,玉摇摇钗燕袅
鸡翘。一撮儿娇娆,恰蓓蕾丁香萼,又葳蕤豆蔻梢。锦绣额赠新题走蚓惊蛇,丹
青帧摸巧样回鸾舞鹤。
【梁州】惹娇云招嫩雨十二楼前竞赏,唤春风呼夜月三千队里争高。向人前
所事包藏着俏。迷下蔡惑阳城的妩媚,赴高唐闹广寒的风标;冠薛涛压秋娘的声
价,傲冯魁怜双渐的心苗。五陵儿没福也难消,三般儿巧笔也难描。袒春衫似梅
花雪捏就酥胸,忄宝带似藕花风吹来麝脑,沁香汗似梨花露湿透鲛绡。想着,
他自度。更有那家传口授的闲谈笑,记不真咏不到。则除是于入桃源走一遭,恁
时节不落分毫。
【尾声】锦窝巢云屏雾帐重围绕,花胡洞翠槛朱栏巧结缚,况值着媚景明时
畅欢乐。我将他风流窨约,行藏品藻,集主青楼卖弄到老。 赠美人号展香绵杨铁笛为著此号
芳姿腻腻娇,素质娟娟净。绸缪无限絮,继续有余情。天付聘婷,纯一味温
柔性,纵丹青画不成。软耨耨堪宜梅雪同心,白霭霭不与梨花共影。
【梁州】价重如齐纨鲁缟,名高似蜀锦吴绫。惜花人故把杨花并。缠联月户,
缭绕云屏。昏迷客路,散漫邮亭。最关情眼底飘零,不由人掌上奇擎。飞晓日又
不曾牵惹游丝,随暮雨又不曾沾粘落英,趁东风又不曾化作浮萍。几回,自省。
过青春谁与怜薄命,空落得旧名姓。人都道十二瑶台夜不扃,逃下的飞琼。
【尾声】若能够半丝儿系足为媒聘,煞强似几缕同心结志诚。常记得雪虐风
陵夜初静,孤眠的惯经,知音的试听,有他呵便冻死了梅花愁甚么被窝儿冷。 赠美人
缘底事谪离方丈台,是谁人赚出桃源洞,何日里拜辞王母殿,甚风儿吹下广
寒宫。蓦地相逢,眼眩乱魂飞动,方信道仙凡路可通。内家妆都猜是金屋婵娟,
前生业却做了青楼爱宠。
【梁州】蝤蛴颈净匀粉腻,豆蔻梢软耨春浓。更说甚海棠露胭脂重。绡袖
薄腕笼温玉,酒颜酡肋晕轻红;腰束素裙拖暖翠,眼涵秋水点星瞳;口脂薰兰气
冲冲,胸酥渍香汗溶溶。登卧榻一团儿雪压氍毹,对妆台一朵儿花生镜容,浴温
泉一泓儿水浸芙蓉。自疑,自懂。只恐是沾云雨阳台梦,梨园内万人众。烟月
排场锦绣丛,别样春风。
【尾声】赋佳人的宋玉堪题咏,图仕女的崔徽枉费工。常记席上樽前那些陪
奉:喜孜孜捧着玉钟,娇滴滴擎着笑容,端的是压尽人间丽情钟。 自省
黑漫漫离恨天,白漭漭迷魂海,闹垓垓风月场,昏惨惨雨云台。天与安排,
都变做莺花界,单捱着聪明的撞入来。枕畔言糊突了胸襟,花下酒消磨了气色。
【梁州】我待将玩江楼风流再整,谁敢把丽春园时价高抬?这几般儿症候年
年害。并头莲忙折,连理树勤栽;相思梦不觉,囫囵谜难猜。眼睛儿盼行云不离
书斋,魂灵儿趁东风先到花街。知自知虚脾枉自温存,笑自笑讪脸偏禁打掴,怪
自怪痴心不服烧埋。待开,怎开?我则索皂纱巾护了天灵盖,赤紧的做鸨儿不宽
大。但有个权势的姨夫大块子扌只,便笑靥儿攒腮。
【尾声】妆孤的已受王魁戒,赡表的休夸双渐才,这两年达时务的玄机恰参
解。朱颜半衰,黑头渐白,犹兀自无倒断的着迷甚时改。 赠人
麒麟阁上臣,虎豹关中将,名高金殿客,贵压紫薇郎。玉立昂昂,捧日月光
天象,保山河壮帝乡。紫金梁稳架沧溟,白玉柱高擎庙堂。
【梁州】醉仙桃九重春色,拂御炉两袖天香。风云豪气三千丈。咳唾落珠玑
颗颗,佩环摇金壁锵锵。奇略饱阴阳经诀,壮怀吞星斗文章。拥貔貅银锁光芒,
动龙蛇赤羽飞扬。叱咤间净中原狐兔之尘,指顾里荡西戎犬羊之党,笑谈中定边
陲蛮貊之邦。远方,近方。黄童白叟知名望,一人下万人上。铁券丹书姓字香,
万代辉光。
【尾声】玉醍醐金叵罗肉台盘气氤氲香霭莲花帐,锦罘ぜ珠珞索翠氍毹光灿
烂春生柿蒂堂,曾受用风流黑头相。对槐阴昼长,趁荷香晚凉,一派笙歌洞天里
响。 同前意
巍巍九鼎臣,落落三台位;飘飘七步才,密密五兵机。门第相辉,俯仰谐天
意,经纶合圣规。书架插三万旧日牙签,武库列十二清霜协戟。
【梁州】翰墨夺人间锦乡,咳唾落天上珠玑。统雄藩肃镇西南裔。紫泥诏符
分铜虎,碧油幢纛散红嫠。金麒麟绣蒙锁甲,玉暾龙带束宫衣。八卦营细柳深迷,
五方旗铁马骄嘶。喜的是沙漠空狐兔尘清,江海静鲸鲵浪息,宫殿高燕雀风微。
授之以德,用之以礼。因此上太平天子无为治,咫尺间九重内。唤得春来草木知,
万物熙熙。
【尾声】金瓯应已藏名讳,麟阁终当绘像仪。寄语公明董狐笔:比及待论功
赐邑,铭彝勒石,先筑沙堤四十里。 子弟每心寄青楼爱人
芳卿细细听,贱子明明道。雨云虽念想,风月不坚牢。月夜花朝,两地成耽
阁,虚飘飘何日了。吐蛛丝锁不住蝶使蜂媒,衔燕泥对不就鸾窝凤巢。
【梁州】怕不道甜腻腻恩情怎舍,瞒不过响礼法难饶。赤紧的一身万事
萦怀抱。椿萱衰迈,松菊萧条;云山缥缈,烟水迢遥。则落得莺燕呼招,怎能够
琴瑟和调。恰便似刘晨误入天台,洛浦神游汉皋,裴航梦断蓝桥。几遭,窨约。
既知休怕甚莺花笑,便做道娶之后怎发落。少不得留与青楼做散乐,倒不毛
毛。
【尾声】从今后休将锦字传青鸟,谩把纶竿钓巨鳌。不是我巧语花言厮推调,
恁如今模样正娇,年纪儿又小,则不如觅个知心俊孤老。 劝妓女从良
丽春园有世情,鸣珂巷无公论。爱村沙欺软弱,嫌文墨笑温纯。别是个家门,
饱暖随时运,诙谐教子孙。伴风姨陪月姊甚日辞栅,觅花钱偿酒债何年证本?
【梁州】妆镜里暗暗的添了白发,酒席上飘飘的过了青春。急回头已是三十
尽。粉褪了杏肋桃脸,涎干了瓠齿樱唇,尘暗了锦筝银甲,香消了彩扇罗裙。恁
待要片时间拔类超群,则除是三般儿结果收因。招一个莽庄家便是良人,嫁一个
穷书生便是孺人,苫一个俊孤答便是夫人。小生,暗忖。如今的这女娘每一个个
口顺心不顺,多诡诈少诚信。直待红鸾活现身,可不道好景因循。
【牧羊关】试点检莺花薄,细摩挲烟月文,真乃是有奇花便有东君。玉箫女
结韦皋两世丝萝,苏小卿配双渐百年眷姻。谢天香遂却耆卿志,李亚仙疼煞郑生
贫。薛琼英大享着奢华福,韩素梅深蒙雨露恩。
【尾声】你毕罢了柳衢花市竹歌阵,我准备着凤枕鸳帏锦绣ブ,纵然道板障
的娘娘有些生忿,明放着玉镜台主婚,金花诰保亲,不愿从良的也算得个蠢。 同前意
红舒脸上桃,翠展眉间柳,粉溶肌雪腻,绿鬓云稠。一撮儿风流,带绾金
双扣,鞋弯玉一钩。紫绡浓红锦腰围,银股钏珍珠臂鞴。
【梁州】据标格是有那画阁兰堂的分福,论娇羞怎教他舞台歌榭里淹留。则
落得闲茶浪酒相迤逗。昨日逢故友柳边开宴,今日送行人花下停舟。这壁急攘攘
莺招燕请,那厢闹烘烘蝶趁蜂逐。恰则待热心肠相和相酬,也合想业身躯无了无
休。我劝你滑擦擦舍身崖想个逃生,昏惨惨迷魂洞寻个罢手,碜可可陷入坑觅个
回头。二旬,左右。他则想春花秋月常依旧,试与恁细穷究。我则索先盖座春风
燕子楼,省也么叶落归秋。
【尾声】谁不知苏卿已嫁双通叔,王氏偏怜秦少游,咱两个没添货的姻缘厮
成就。天长地久,鸾交凤友,再不教你鸣珂巷路儿上走。 赠玉芝春
休言雨露恩,不假阳和力。自天能长养,无地可栽培。素质香肌,正遇承平
世。比春花别样奇。光腻腻出落着风流,清淡淡包含着旖旎。
【梁州】人都道秦弄玉生成标格,我猜是许飞琼托化的容仪。谁承望天风吹
落莺花地。承德墀无缘拜识,甘泉宫有句褒题。谢安石多曾称誉,夏黄公聊得充
饥。向花神试问个真实,检春工自有个高低。风韵似软刺答石上猗兰,雅淡似矮
婆娑朋中老桂,温柔似瘦伶仃雪里寒梅。有谁,认得。九茎三秀真祥瑞,相遇是
何日?但能够分得微香到酒杯,不枉了玩赏忘归。
【尾声】既不能贮雕盘蒙锦帕擎将手掌轻怜惜,也消得依画阁近兰堂着个栏
干谨护持,春日春风莫虚费。你道是浮花浪蕊,他须是灵根异卉,恰不道一夜琼
花落无迹。 赠玉马杓
堪嗟和氏冤,莫讶相如亻赞。既酬雍伯志,何虑范增嫌。想像观瞻,雀尾样
其实欠,鸬鹚名空自慊。有十分资质温柔,无半点尘埃ネ染。
【梁州】温石铫徒劳磨渲,镔铁钩本费锤钳。似剜出一团酥更压着琼花艳。
泼新醅分开绿蚁,掬清波荡碎银蟾。美声雀高如金斗,秀名儿近似珠帘。富石崇
犹兀自等等潜潜,穷双渐也则索让让谦谦。舀得些拔禾侠家计空空,兜得些偷花
汉劳心冉冉,敲得些贩茶商睡思恹恹。莫言,咱媚谄。丽春园谁敢待争奢俭,漾
不下抱不厌。纵然道夏鼎高彝休将做宝贝店,也不似他情タ。
【尾声】好向他万花丛里为头儿占,休教人百味厨中信手儿拈,恁时节添不
上风流洗不了瑕玷。倾城的貌甜,连城的价添,稳情敢玩瓢戏的西施望风儿闪。
莲卿王氏者,楼居潇洒。余颜之曰:楚馆凝眸,其所寄意
无乃对景兴怀、欢情离思而已。因其请题,遂书此以赠焉
碧玲珑透月窗,锦灿烂藏春帐;黑揩摸乌木几,金嵌镂紫檀床。一片风光,
胜压莺花巷,名高烟月乡。绣ブ舒并宿鸳鸯,雕奁锁双飞凤凰。
【梁州】龙脑香生瑞霭,虾须帘卷斜阳。动芳情多为凭栏望。翠柳黄鹂个个,
青天白鹭行行;锦缆牙樯簇簇,金沙流水茫茫。但凝眸渐觉彷徨,忽萦怀又索包
藏。锁魂桥芳草地几度离别,折柳亭拂尘会几场宴赏,落花天残灯夜几样思量。
话长,意长。止不过弱红娇黛相偎傍,酝酿出雨云况。可知道宋玉当年为发扬,
赋作《高唐》。
【尾声】金鸾横玉燕都夸楚馆风流样,蟠龙髻扫翠蛾全胜巫山窈窕娘。常
言道鉴柳评花不虚诳;似恁的兰心蕴芳,莲姿喷香,不由人浓蘸着霜毫细褒奖。 咏素蟾
噪晴蛙枉叫嚎,脱壳蝉徒悲泣。缩项鳊空跳跃,攒毛猬甚稀奇。将《山海经》
穷推,出乎类拔乎萃,不在山不在水。美名儿满天上人间,耍性儿傍星前月底。
【梁州】剔秃驾彩云恰离瀛海,明滴溜趁清风又下峨嵋。捣率霜仙药的玉
免偏知契。杨柳楼心弄影,娑椤树底扬辉;竹叶樽中荡漾,梅花窗外徘徊。煞强
似负灵蓍九尾神龟,更压着叫扶桑三足天鸡。活不刺大罗仙手掌上奇擎,矮婆娑
翰林客砚池边侍立,滑出律广寒娇寝帐里追陪。我知,就是。多管是玉之精魄之
气,那雅淡那清致。可知道天宝三郎爱羽衣,险送了华夷。
【尾声】婵娟不假铅华力,莹洁应夺造化机。相思病的郎君若医治,也不索
评诊脉息;更不须调和药石,但能够半点儿琼酥救了你。 嘲妓名佛奴
不参懵懂禅,先受荒淫戒。才离水月窟,又上雨云台。东去西来,还不了众
生债。竟说甚空是空色是色,苫亻来呵四十八愿叮咛咒誓,巴镘呵五十三参容颜
变改。
【梁州】恰着老达磨泛芦叶浪游海国,又沾上阿罗汉觅桃花远访天台。那
里问当年摩顶人何在?超度了千家子弟,坐化了万种婴孩。则落得拈香剪发,早
难道灭罪消灾。虽然道村冯魁布施些钱财,须不曾俏双生供养在书斋。卧房儿伽
蓝殿般收拾,客院儿旃檀林般布摆,门面儿龙华会般铺排。左猜,右猜。这渥洼
水不曾曹溪派,那庵门甚宽大。但有庞居士般人儿莽注子扌只,便慧眼睁开。
【尾声】张无尽气冲冲待打折了莺花寨,韩退之嗔忿忿敢掀翻烟月牌,赢得
虚名满沙界。风月所状责,教坊司断革,迭配与金山寺江中贩茶客。 言志
自怜王粲狂,莫怪陈登傲;不弹贡禹冠,谁赠吕虔刀。十载青袍,况值烟尘
闹,事无成人半老。黄金台将丧斯文,白玉堂空怀故交。
【梁州】看鞍马上诸公衮衮,听刀戈下众口嗷嗷。因此上五云迷却长安道。
曳裾休叹,投笔空焦;题桥谩逞,击楫徒劳。直钩儿怎钓鲸鳌,闷弓儿难谢鹏雕。
喜的是砚池内通流着千丈沧溟,诗卷里包藏着九重宣诏,书楼上接连着万里云霄。
虽道是浅识,寡学。这几篇齐鲁论也不下于黄公略,捻吟髭自含笑。矫首中天日
正高,豪气飘飘。
【尾声】闲拈斑管学张草,静对黄花诵楚骚。等待新雁儿来时问个音耗;若
说道董仲舒入朝,公孙弘见招,看平地风雷奋头角。 赠人
雍容黄阁姿,卓荦青云态。彷惶忧国志,慷慨济时才。奉诏西来,冲阐雾临
边界,驾天风下凤台。正正旗堂堂阵蛇鸟争辉,辚辚车萧萧马风云动色。
【梁州】展其韬施其略孙吴是法,依于仁行于义周孔为怀。经纶迥出诸藩外。
八阵旗春营柳暗,七重围夜帐莲开。六钧弓晓星迸激,双龙剑秋水磨揩。转储胥
周馈饷掌上裁划,抚疲赢得营逸阃外驱差。玉免毫挥翰墨学足三冬,紫鸾诰叙勋
旧恩封三代,丹墀陛列斑资步近三台。伟哉,盛哉。况赖着巍巍圣德乾坤大,露
布驰玉关外。倒挽银河下九垓,净洗氛埃。
【尾声】录丰功褒盛绩班班拟见铭钟鼐,著芳声垂后代历历终期绚竹帛。若
报道东阁门前不妨碍,借尺地寸阶,进一言半策,那时节吐气扬眉拜丰采。 同前
心怀雨露恩,气禀乾坤秀。读书尊孔孟,许国重伊周。得志之秋,文艺武皆
穷究,正青春正黑头。孙吴略切切于心,齐鲁论孜孜在口。
【梁州】瞻日月抬头是凤阙,会风云闲步是龙楼。真乃是祖生鞭不落刘琨后。
千金买剑,五彩赞裘,七重围帐,半万戈矛。跨锦鞯丝辔骅骝,拥铁关金锁貔貅。
论文时芸窗下摘句寻章,论武时柳营内调丝弄竹,消闲时花阴外打马藏阄。五行,
本有。功名二字俱成就,能燮护会消受。一寸丹心答冕旒,愁甚么建节封侯。
【尾声】烟沮青海城边堠,兵洗黄河天上流,庆祸皇图万年寿。蛮夷殄收,
戎狄遁走,恁时节描入麒麟画工手。 同前意
汪汪江海心,落落云霄志。昂昂经济才,矫矫郎庙姿。阃外行司,暂把牛刀
试,播芳声雷贯耳。匣中剑冰涵秋水芙容,腰间带银盘花荔枝。
【梁州】烽烟息朝廷有道,簿书闲公馆无私。笑谈间唤得春风至。昆季雍雍
穆穆,友朋切切。礼法兢兢业业,规模念念孜孜。了公家无甚萦思,追欢乐
有甚推辞。猎西山金仆姑锦袋雕弓,宴东阁银凿落琼筝宝瑟,游南陌紫叱拨玉辔
青丝。丈夫,似此。多管是胸中寸地平如砥,嘉瑞已天赐。庭上兰孙与桂子,雨
露滋滋。
【尾声】于亲已足平生志,许国应当少壮时,虽孝场忠但如是。抱金曳紫,
承恩奉旨,稳情取勋业班班照青史。 云山图为储公子赋
长歌《陟岵》诗,饱玩《闲居赋》。倦听花底莺,羞见树头乌。日月居诸,
又觉春光暮,对云山强自娱。白云边盼不见白雁来宾,青山外等不至青鸾寄语。
【梁州】云去也山容妥贴,云来也山色模糊。真乃是一声杜宇不知处。青隐
隐浑疑太华,白漫漫错认蓬壶。黑黯黯难分吴越,绿迢迢不辩衡庐。云连山远近
相逐,山连云上下相续。可知道陆士衡酝酿做文章,王摩诘收拾在肺腑,狄仁杰
迤逗出嗟吁。老夫,道欤。既思亲便索寻亲去,愁险峻惮劳苦。却把云山写作图,
于理何知。
【尾声】心头菽水何时足,眼底云山甚处无,寸草春晖自今古。但能够青山
共居,白云共锄,才与云山做得主。 黄鹤楼
峥嵘倚上流,突兀当雄镇。高明临大道,迢递接通津。从去了鹤山仙人,千
载无音信,丹青再创新。架飞楹联走拱不下班亻垂,敞天窗赞藻井堪攀翼轸。
【梁州】龟背织牛帘闪闪,鸳翎碧瓦鳞鳞。雕阑一目无之尽。洞庭半掬。
云梦平吞。荆襄俯瞰,汉沔中分。长空远水,光风霁月纷纷。吕岩笛夜夜闻
音,陶令柳年年报春,崔颢诗句句绝伦。后人,议论。都道是物华胜压东南郡,
况与洞天近。降节琅敖度彩云,万象腾文。
【尾声】汀花岸草春成阵,沙鸟风帆幕作群,我待要闲蹑金梯散孤闷。仰之
北辰,俯之大坤,气势高寒立不稳。 梦游江山为友人赋
蜀道难长怀李太白,庐山高每羡欧阳叔。江曲折多询郭景纯,海周遭曾问木
玄虚。吠刚来混一皇舆,万里神游去,何须觅坦途,脚到时选胜寻幽,眼落处兴
今慨古。
【梁州】图得些风月情长沾肺腑,赢得些是非尘不到襟裾。分明记得经行处。
蹑苍梧冲飞彩凤,扣扶桑撼动金乌,登雁宕惊潜木客,涉龙门啸起天吴。又不比
悠悠泛一叶黄芦,飘飘跨两足青凫。散诞似李元贞松阴内干禄求名,逍遥似赵师
雄梅花下开樽按舞,廓落似淳于棼槐柯上架室安居。遮莫五湖,四渎。钓竿直拂
珊瑚树,天地阔渺无路。撞入仙翁白玉壶,知他是紫府也那清都。
【尾声】湿淋浸满身香露侵毛骨,吉玎过耳清<风贵>响琚,蓦然地睁破
双眸飒然悟。尚兀自炉烟馥郁,灯花恍惚,月在梧桐画阑曲。 题心远轩
不从方外游,且向寰中住。但能通大道,何必厌亨衢。吾爱吾庐,选得陶诗
句,楣间籀字书。黄庭静玩之无穷,灵源溢探之不足。
【梁州】七窍达八荒广漠,一帘隔万里空虚。谁不知方寸地无多物。玄参黄
老,易论程朱。诗敲险怪,棋较赢输。不闻满耳喧呼,只宜竟日跏趺。恰枕肱悠
悠梦绕华胥,不动脚默默神游洛浦,才合眼飘飘身在蓬壶。本无,间阻。山林城
市俱同路,解到此中趣。便觉吾生百虑疏,遐迩何如。
【尾声】光风转蕙春生户,幽草生香月到除,不离蒲团三二步。休道星蹿月
窟,遮莫天关地轴,垂拱之间在环堵。 赠儒医任先生归隐先生善写竹
江湖老姓名,风月闲人物。文章新制作,礼乐旧规模。暮景桑榆,杏林好春
无数,橘泉甘乐有余。一丝风曾钓鲸鳌,九转丹恰成龙虎。
【梁州】核老聃千言道德,问安期万劫荣枯。常则怕白云引入青山去。包含
丹篆,簸弄明珠。逍遥巾帻,懒散襟裾。虽不曾指南阳卖却茅庐,少不得傍东湖
苫个屠苏。菊花枕满头香雾氤氲,梅花帐满鼻香风馥郁,芦花被满身香雪模糊。
淡然,自足。可知道黄金不卖长门赋。将千亩渭川竹,写作江南烟雨图,畅不尘
俗。
【尾声】清溪道士为宾主,东里先生问起居,谢却红尘是非路。清茶自煮,
浊醪旋沽,日日高歌紫芝曲。 卓文君花月瑞仙亭
青袅袅垂杨近画楼,响溅溅暗水流花径。轻香风翻翠幌,光辉辉银或射
雕楹。悄悄冥冥,出绣户瑶阶静,步苍苔罗袜冷。翠袖薄玉臂生寒,金翘乌云
堕影。
【梁州】横斗柄珠星灿灿,界勾陈银汉澄澄。恰行到梧桐金井潜身儿听。晃
绿窗十分月色,隔幽花一片琴声。明出落求鸾觅凤,暗包藏弄燕调莺。一字字冰
雪之清,一句句云雨之情。卖弄他穷书生酸溜溜调美才高,迤逗的俊女流急穰穰
宵奔夜行,辱末煞老丈人羞答答户闭门扃。那生,可称。一峥嵘便到文园令,富
贵乃天命。长门赋黄金价不轻,可知道显姓扬名。
【尾声】恰待要班趋北阙身初定,谁承望梦入南柯唤不醒,且休将《史记》
里源流细参订。传奇无准绳,关目是捏成,请监乐的先生自思省。 素兰
春含九畹芳,香得三湘瑞。名高萼绿华,梦入郑燕吉。虽然道满目芳菲,
不与群芳比,群芳自不及。有十分雅态幽姿,无半丝浮花浪蕊。
【梁州】包哑谜栽排了陶谷,寄情诗奚落煞张硕。谁承望天风吹落莺花地。
紫芽荏苒,丹颖葳蕤。檀心馥郁,翠带离披。也不弱月桂寒梅,便休题杜若江篱。
日烘烘有绿艳醺酣,风似翠裙摇曳,露浸浸如香汁淋漓。若非,异卉。楚大
夫怎肯纫为佩,更一般甚清致。纬天经地鲁仲尼,也将他演入金徽。
【尾声】既不着珠帘翠幕深遮闭,也消得绣槛雕栏谨护持,试与知音细论议。
恁待要笔尖上品题,眼皮上爱惜,则除是描入明窗画图里。 赠草圣
括造化攒成赤免毫,挽沧溟磨彻乌龙墨。灿日月光摇玉版笺,吐烟云香彻紫
英石。四宝清奇,潇洒芸窗内,风流莲帐底。念孜孜八法八诀,意悬悬六书六体。
【梁州】指其掌画其腹云崩露垂,得之心应乎手电走风飞。天然一笔无穷意。
秋蛇春蚓,野鹜家鸡。跳龙卧虎,渴骥狰猊。有阴阳偃仰精微,无偏枯向背支离。
乐毅论太名箴敷扬出忠烈之风,逍遥篇孤雁赋酝酿出神仙之气,曹娥碑告誓文摸
临出孝弟之规。遮莫醒兮,醉兮。一挥一洒非游戏,干喜怒系明晦。可知道笔冢
累累墨作池,名重京畿。
【尾声】谁不道十年草圣通三味,我则知一日偷闲测万机。常闻得青琐高贤
自评议:比着那颜真卿健笔,王右军妙迹,真乃是一色长天共秋水。 题友田老窝
桧当轩作翠屏,月到帘为银烛。柳绵铺白毡,苔线展紫绒<毛莫>。四壁萧
疏,若得琅护,何须藤蔓补。听了些雨打窗下芭蕉,看了些日照盘中苜蓿。
【梁州】破陆续歇两肘疲童洒扫,烟刺答漏双肩老妪供厨。主人自得其中趣。
隔墙贯酒,凿壁观书。拾薪煮茗,赁辅载蔬。雀堪罗忙煞蜘蛛,鼠无踪闲煞狸狐。
寂寞似莱鞠县范史云琴堂,虚敞似临邛市马相如酒垆,潇洒似浣花溪杜子美茅庐。
坦然,自足。地里拨灰吟出惊人句。想石崇在金谷,止不过锦障春深醉绿珠,
今日何如?
【尾声】送将穷鬼出门户,描取钱神入画图。但能够半点阳和到乔木,管城
子进取,孔方兄做主,翻盖做十二瑶台列歌舞。 赠教坊张韶舞善吹箫
露万籁沉,风淡淡三更静。天空空千里水,月朗朗一壶冰。蓦闻得何处
箫声,一曲中和令,其音协九成。呜呜然赤水龙吟,呖呖兮丹山凤鸣。
【梁州】动蜿蜒幽壑潜蛟舞跃,感婵娟孤舟嫠妇魂惊。多管是秦台箫史曾参
订,低韵吐游丝,柔腔度细缕萦萦。颠狂非落梅之趣,悠扬有折柳之情。七
数明指法轻清,六律谐音品和平。从今后柯亭馆桓叔夏再莫横笛,昭阳殿薛寿宁
何劳按筝,缑山岭王子晋不索吹笙。兀的般老成,艺能。不枉了天风吹散人间听,
消郁闷发清兴。占断梨园第一名,非雀非矜。
【尾声】仰龙楼瞻风阙孜孜念念钦皇命,趁班随鹜序落落疏疏见乐星,更
那堪一点丹诚抱忠敬。常言道有麝自馨,无蓝不青,稳情取大宠着恩光辉乡井。 送车文卿归隐
轻帆滟堆,瘦马峨嵋栈。颠风洋子浪,落日太行山。地窄天悭,长恨归田
晚,徒悲行路难。平地间宠辱关心,故纸上兴亡在眼。
【梁州】愁甚么负郭田无二顷,喜的是依山屋有三间。一回头万事都疏懒。
绿蚁樽浇平磊块,紫鸾箫吹散愁烦。黄齑菜养成脾胃,青精饭驻定容颜。岸天风
乌帽翻翻,拂埃尘布袖斑斑。比鹤上人不驭飙轮,比山中相不登仕牌,比壶内翁
不炼金丹。得闲,且闲。多管是鹿门庞老为师范,摆脱了是非患。恰便似高枕着
昆仑顶上看,人海波澜。
【尾声】落红阶砌胭脂烂,新绿门墙翡翠寒,安乐窝随缘度昏旦。伴几个知
交撒顽,寻一会淦樵调嗲,终日家龙凤团香免毫蘸。 赠会稽吕周臣
三千丈萧萧白发生,七十岁楚楚青衫旧。抱经纶无官朝北阙,买梨锄有子事
西畴。气禀清修,玉耸双肩瘦,胸涵一镜秋。蹑天根深地脉秘诀深微,步诗坛入
酒社精神抖搜。
【梁州】瞻胜迹蓬莱山不离眼底,避危途太行路长在心头。将古今吏稳都穷
究。慕谢安高迈,羡陶令归休,爱戴逵洒落,学贺老风流。文房艺苑偏游,药栏
花径清幽。披览著种陵书半窗星斗光芒,张玩着辋川图四壁烟云驰骤,拨刺着峄
阳琴一帘风雨飕飕。淡然,自守。全胜他归山指破麻袍袖,能燮护会消受。高卧
元龙百尺楼,万事悠悠。
【尾声】恰能够天涯萍水同携手,谁承望江上莼鲈又买舟,少不的再叙离怀
那时候。连床秉烛,隔离唤酒,夜雨呼童剪春菲。 赠钱塘镊者
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但识破毫厘千里谬,才知道四十九
年非。这归去来兮,明是个安身计,人都道陶潜有见识。谁恋他花扑扑云路功名,
他偏爱清淡淡仙家道理。
【梁州】打荡着临闹市数椽屋小,滴溜着皱微波八尺帘低。自古道善其事者
先其器。雪锭刀揩磨得利,花镔镊抟弄得轻疾,乌犀篦雕锼得纤密,白象梳出
落得新奇。虽然道事清修一艺相随,却也曾播芳名四远相知。剃得些小沙弥三花
顶翠翠青青,摘得些俊女流两叶眉娇娇媚媚,镊得些恍郎君一字额整整齐齐。近
日,有谁?闲遥遥寄傲在红尘内,虽小道莫轻易。也藏着桑柘连村雨一犁,到大
便宜。
【尾声】从今后毕罢了半窗夜月樗蒲戏,洗渲了两袖春风蹴リ泥,兀的般自
在生涯煞是伶俐。你觑那蝇头利微,也须是鸡肋味美,不承望陈七子门徒刚刚的
快活了你。 旅中自遣
锦囊宽闲凤琴,宝匣冷藏龙剑。篆香消闲翠鼎,书卷广乱牙签。郁闷恹恹,
青琐论无心念,紫霜毫不待拈。赢似老文园病渴的相如,寂寞如居海岛伤怀的
子瞻。
【梁州】看白支闲出岫频移净几,爱青山正当窗不卷疏帘。客房儿冷落似邯
郸店。心滴碎铜壶青漏,耳愁闻铁马虚檐。肠欲断阶前夜雨,梦初回屋角秋蟾。
一片心远功名无甚沾粘,两只脚信行藏有甚拘钤。经了些摧舟楫走蛟鼍鲸窟波翻,
行了些坏车轮被虎豹羊肠路险,过了些连云梯绝猿犹鸟道峰尖。静中,自检。事
无成志不遂人情欠,休施逞且妆俭。但得个小小生涯足养廉,甘分鳞潜。
【尾声】能文章会谈化才高反被时人厌,守清贫乐清闲运拙频遭俗子嫌。有
一日际会风云得凭验,那时节威仪可瞻,经纶得兼,正笏垂绅远佞谄。 题白梅深处
罗浮山接渺茫,大庾岭横冥,凌风台迷汗漫,却月观阻迢遥。意会神交,
想得到行得到,一逢春一遇着。蕊疏疏花密密蓓蕾葳蕤,干盘盘枝挺挺槎牙夭
矫。
【梁州】品藻着世上色无瑕疵的雅淡,评论着天下花无褒贬的孤高。长记得
看花时有几样儿堪称道。露点滴珠融腻粉,烟朦胧翠护轻绡;风摇曳香飘麝脑,
雪模糊玉压琼瑶。厌桃杏灼灼夭夭,伴松篁洒洒潇潇。何水曹一生心爱得绸缪,
林和靖两句诗联得妙巧,宋广平八韵赋撰得风骚。想度,暗约。我猜似梨云一片
连溟漠,指顾间自吟啸。但则觉花气氤氲袭毳袍,白茫茫万树千条。
【尾声】全不似梦游东海寻三岛,真乃是身在西湖过六桥。嘱付那羌管呜呜
莫吹落,等待着籁声悄悄。月华皎皎,看一会疏影横斜到清晓。 题崇明顾彦升洲上居
潮生玉马来,沙涌多鳌动,水天涵上下,浦溆控西东。四望无军,一片玻璃
莹,梯航万里通。荡炎蒸青风六月凄凄,翻渤渤红桃浪三春光。
【梁州】近睹着扶桑野阳乌闪烁,遥认着蓬莱山烟霭冥蒙。天然幽胜堪题咏。
柔桑蔼蔼,秀麦,丹椒簇簇,碧苇丛丛。闹人烟生意从容,旧家风礼节谦恭。
宴斯堂何时不馔鸡豚,居是洲何代不生麟凤,观于海何年不化鱼龙。岁丰,廪充。
喜的是年年布俗催春种,知用舍,厌迎送,睡彻东窗日已红,乐在其中。
【尾声】幽寻不索桃源洞,高卧何须太华峰。但得个留心诵周孔,研朱墨训
蒙,买犁锄务农,则消得赡老良田二三顷。 桧轩为越中沙子正赋
得指教三迁好住居,便栽培十丈深根蒂。能借取四时春造化,似生成一片翠
屏帷。大刚是即景成规,直干攒楹密,横柯压栋齐。但将翰墨褒题,不假丹青绘
饰。
【梁州】青郁郁柏叶松姿备体,浓馥馥芝香术气沾衣,更几般天然景趣谐人
意。风过处线篁嘹亮,月来时金碧光辉。檐露洒珠玑点滴,篆烟生紫黛霏微。虽
无华丽芳菲,端实萧爽清奇。奢可效七松家绮幕围风,清末让五柳庄黄花绕篱,
贵不幕三板堂画戟当扉。料伊,所为。单指着岁寒眼底为交契,况值太平世,一
样肝肠似铁石,愁甚么雪虐霜欺。
【尾声】映疏帘笼曲槛盘旋着夭矫蛟龙势,傍危栏依短砌踞耸著狰狞虎豹威。
我试将过眼的风光自评义:十万户会稽,八百里鉴水,纵有些亭台则是栽桃李。 题支巢
揽将天上云,占却山头树。树头云,云底树扶疏。从此归欤,混沌安心
素,微茫隔世途。既然以天地为家,甘分与林泉做主。
【梁州】门径窄何须绰楔,栋梁低不用楔栌。道人自有安排处。慢慢构造,
巧巧支吾。宽如舴艋,小若屠苏。但知变化须臾,还看聚散何如。云生也四壁模
糊,云定也一团蓊郁,云收也万象空虚。羡乎,笑乎。方信道白云本是无心物。
谁把此中趣,淡淡浓浓写作图,畅不尘俗。
【尾声】听琴鹤至分床宿,送果猿来借榻居,绝胜当年老巢父。怡然自娱,
恬然自足,再不从龙化甘雨。 赠王观音奴
出西方自在天,受南海无边愿。宫妆宜水月,香步绕金莲。体态婵娟,绿杨
柳腰枝软,白鹦哥声调圆。结百千万种良因,示五十三参化显。
【梁州】苦海阔色空未脱,爱河深情欲相牵。今生不了前生愿。慈悲厚德,
救苦真言。枝头甘露,瓶里香泉。旃檀林夜月娟娟,雨花台苦恨绵绵。宰官身进
宝归依,善男子赍金募缘,老门徒统镘参禅。上天,下天。龙华会里曾相见。叩
庵门觅方便,指点其中意已穿,心绪悬悬。
【尾声】拟将樱络千金串,结就珍珠七宝钿,世世生生作姻眷。脱空心告免,
指山盟是谝,则不如剪发燃香意儿远。 赠王善才
手曾将千眼佛绿柳瓶,身曾侍七宝岩红莲座。目曾瞻普陀山金孔雀,心曾记
南海岸玉鹦哥。为一念差伪,离水月观音阁,堕风尘锦绣窝。金刚刃怎割愁肠,
甘露水难消业火。
【梁州】记五十三参坎坷,爱四十八愿奔波。舍身崖一片声名大。风魔了智
广,病愁煞维摩,痴迷了六祖,调笑煞弥陀。则为你送行云两点秋波,舞香风六
幅春罗。至诚人但焚香有愿须酬,兹悲友既剪发随缘较可,薄情郎纵赍金没福难
合。俺呵,敢么?多持七宝香璎珞,既相承怎空过。指点其中自忖度,于意云何?
【尾声】衣垂舞凤珍珠颗,髻挽蟠龙翡翠螺,粉脸生香衬莲萼。龙华会见他,
香音国有他,誓结今生善因果。 赠妓宋湘云
送飞琼下九天,驾弄玉游三岛,伴巫娥临楚台,偕裴子赴蓝桥。景物飘飘,
翻覆手谁能料,去来心怎忖度。舞香风暮暮朝朝,酣雨花花草草。
【梁州】飞南浦新愁冉冉,度东墙旧恨迢迢。锁朱楼不放春光晓。记崔生密
约,感苏子寂寥;任酸斋笑谑,怪杜牧粗豪。果无心不趁轻薄,若随风一任低高
云呵您休得蔽蟾宫妒嫦娥夜色娟娟,云呵您休得横秦岭使退之忧心悄悄,云呵您
自合下巫山感襄王魂梦飘飘。想着,念着。梨花枕上闲情绕,既徘徊莫萧索。一
曲清歌驻碧霄,巧笔难描。
【尾声】云呵您片时聚散情虽少,几处飞来恨怎消,日幕江东信音到。休低
迷画桥,休深笼翠阁,则不如为雨为霖润枯槁。 赠妓素兰
散清风烟月中,逞素质风尘内,染一枝春色淡,攒两叶翠痕低。束具含犀,
另一种风流意,比群芳分外奇。俏如荪名重秦楼,娇似芷声扬楚国。
【梁州】天谪下仙葩圣卉,世修来雪骨冰肌。等闲谁许问容易。玉盘儿生长,
锦窖儿栽培。影双双连理,叶小小菩提。幽斋结相宜,赏兰亭修禊闲题。胭脂
瓣洗渲净天香,金花粉调和成玉蕊,素檀心抽拣出柔荑。巧移,俏植。舞蹲一念
腰肢细,解人意。笑杀春风不敢吹。种种相宜。
【尾声】并头莲合欢草多清致,如意朵珊瑚枝有价值,瘦影清香足风味。海
棠娇莫比,芙蓉色怎及?雪窗下玲珑镜儿里。 冬景题情
一轮寒日沉,四野彤云布。九天飞碎玉,万里迸明珠。无语嗟吁,却早年华
莫,那堪岁又徂。纵然有机杼千张,织不就离愁万缕。
【梁州第七】愁一阵一阵阵痴呆了心目,恨一番一番番瘦损了肌肤。大会垓
烦恼在眉尖上聚。锦帏罢设,绣榻慵铺;翠衾闲剩,鸳枕空虚。怪不得活计萧疏,
可知道音信全无。这雪蓝桥路一霎儿迷漫,这风武陵溪一时儿冻住,这云楚阳台
一会儿埋没。全不想旷夫,怨女。闲吟柳絮因风句。你便有一千树梅花香透骨,
也梦不到罗浮。
【骂玉郎】孤眠展转伤情绪,捱玉漏,滴铜壶。花开不管流年度,共谁人拥
红炉,斟绿醑,歌《白苎》。
【感皇恩】冷落了金屋娇姝,寂寞了玉堂人物。这其间老了潘安,瘦了沈约,
病了相如。怕不待勉强须臾,将惜身躯。磕不破玉马杓,解不开愁布袋,摔不碎
闷葫芦。
【采茶歌】几时得笑喧呼,醉模糊,只吃的满身花影倩人扶。同月淹留成间
阻,碧梧栖老凤凰雏。
【尾声】长吁短叹三行度,旧恨新愁几万斛,不证果相思对谁诉。他有那锦
心绣腹,我有那冰肌玉骨,但能够雨尤云那些儿福。
林君复先生故居,苏子瞻学士西湖。六月天,孤山路,载笙歌画船无数。万顷玻璃浸玉壶,夕阳外荷花带雨。
晚春席上
客坐松根看水,鹤来庭下观棋。小砚香,残红坠,竹珊珊野亭交翠。相伴闲云出岫迟,题诗在呼猿洞里。
衣松罗扣,尘生鸳甃,芳容更比年时瘦。看吴钩,听秦讴,别离滋味今番又,湖水藕花堤上柳。飕,浑是秋;愁,休上楼。
春睡
花沾宫额,草香罗带,一春心事愁无奈。感离怀,梦多才,流莺只在朱帘外,午睡正浓惊觉来。挨,金镜台;歪,金凤钗。
感旧
凭高凝眺,临风舒啸,一番春事胡蝶闹。越山高,楚天遥,东风依旧桃花笑,金鞍少年何处了,牢,粗布袍。熬,白鬓毛。
闺思
云松螺髻,香温鸳被,掩春闺一觉伤春睡。柳花飞,小琼姬,一声雪下呈祥瑞,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吓,却是你!
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
路旁碑,不知谁,春苔绿满无人祭。毕卓生前酒一杯,曹公身后坟三尺,不如醉了还醉。
怨离别,恨离别,君知君恨君休惹。红日如奔过隙驹,白头渐满杨花雪,一日一个渭城客舍。
孟襄阳,兴何狂!冻骑驴灞陵桥上,便纵有些梅花入梦香,到不如风雪销金帐,慢慢的浅斟低唱。
笑陶家,雪烹茶,就鹅毛瑞雪初成腊,见蝶翅寒梅正有花,怕羊羔美酒新添价,拖得人冷斋里闲话。
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闾休怪。
浙江亭,看潮生,潮来潮去原无定,惟有西山万古青。子陵一钓多高兴,闹中取静。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瘦形骸,闷情怀,丹枫醉倒秋山色,黄菊雕残戏马台,白衣盼杀东篱客,你莫不子猷访戴?
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黎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
竞江山,为长安,张良放火连云栈,韩信独登拜将坛,霸王自刎乌江岸,再谁分楚汉。
子房鞋,买臣柴,屠沽乞食为僚宰,版筑躬耕有将才。古人尚自把天时待,只不如且酩子里胡捱。
莫独狂,祸难防,寻思乐毅非良将,直待齐邦扫地亡,火牛一战几乎丧,赶人休赶上。
立峰恋,脱簪冠。夕阳倒影松阴乱,太液澄虚月影宽,海风汗漫云霞断,醉眠时小童休唤。
 胡应麟
胡应麟 晁错
晁错 袁宏道
袁宏道 韩愈
韩愈 元好问
元好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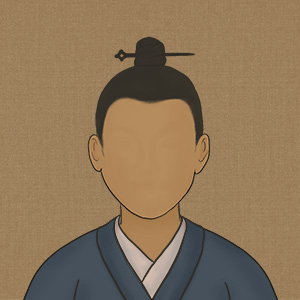 盍西村
盍西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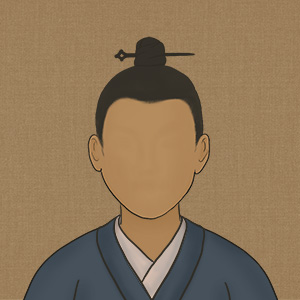 汤舜民
汤舜民 张可久
张可久 马致远
马致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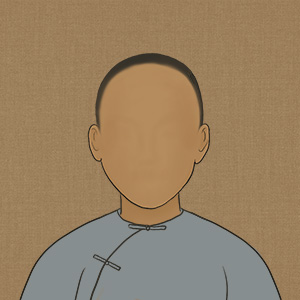 赵令畴
赵令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