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满园春色叩开我的闺房,拨动闺中人的愁思苦想,我心中不尽的怨愁啊,伴随着芳草一天天滋长。花丛里黄鹂在娇婉地啼鸣,薄薄的春雾飘浮在红杏枝上;我在琐窗前无限惆怅。
在思愁中凭栏远望,一双蛾眉又细又长。玉郎还是不回家来,只见柳影斜斜地摇动长廊。柳的飘摇里我的梦魂在幻化,思绪在追逐纷飞的杨花,在天涯里寻觅,在天涯里漂荡。
注释
深闺:女子所居之内室。劳思想:即勤思念。《诗经·燕燕》:“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春芜:春天的杂草。芜,一作“无”,一作“光”。
泥芳妍:在花间萦回。泥,留滞,此有萦回之意。芳妍:指花丛。
琐:一作“锁”。
双娥细:双眉紧锁。娥,一作“蛾”。
砌:台阶。
玉郎:古代女子对丈夫的爱称。
杨花:柳絮。
参考资料:
赏析
此首为思妇之词。开头两句,通摄全词,点明由春色引起春恨。上片主要写春色,下片主要写春恨。上下片仿佛两个相连的画面,全词情景交融。
开始两句十二字,内蕴丰富。“深闺”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少妇,面对恼人春色,不禁情思绵绵。一个“劳”字透露出她那“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的隐痛。由“劳”瘁而怨“恨”,可见其爱之深切。“恨共春芜长”,佳在“春芜”一词含义双重面使全句意味隽永。以春草喻离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远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又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以上“春草”都是本义,没有引申之意。而“恨共春芜长”的“春芜”,除春草本义外,还隐寓行人之意,也就是说此句不仅有闺中人的怨恨随着春草不断增长之意,还含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人越远、恨越长之意。这就深化了诗意,即前人所谓得“句外意”之妙。下面三句写景,以具体意象补充首句“春色”,选取深闺“琐窗前”的视角写思妇所见所闻。“黄鹂娇啭泥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两句宛如五代花鸟画,用笔工细,着色鲜艳。前一句声色并茂,以声为主,富有动势。黄鹂的婉啭娇鸣,似与满园春色而共语。后一句写杏枝倚立于淡淡烟霭中,恬静如画。这春色以黄鹂、红杏为主,缀以群芳的姹紫嫣红,一片暖色,再加上黄鹂悦耳的娇啼,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足喻其美。少妇透过琐窗听见以上春光,当比“忽见陌头杨柳色”感触更为深婉了。上片如从思维顺序出发,触景而生情,则开头两句亦可算是逆笔。
从上结至过片,时空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凭阑”句既自成画面,又未断意脉。原来闺中人被春色所吸引,不满足于隔窗观花,她轻移莲步,款款伫立于阑干旁,含愁凝眸。“双娥细”,以秀眉的细长以形容其青春貌美。“‘柳影斜摇砌”,是思妇凭阑所见,也是下片唯一景语,寥寥五字,一波三折,确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表层意思是柳条之影因风吹斜而摇曳于台阶,但其中还隐含摇落了杨花、杨花飘落于“砌”两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浓缩于五字句中,写得极密。五字中没有“杨花”字样,而于下文显现,是诗人匠心所在。下文思妇的内心独白,由上片的蓄势,直至此句才引发出来。从杨花的摇落,联想自己红颜将凋零,所以她痛苦地唱出了全词的最强音:“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和开头暗相呼应。她终日盼不回丈夫,怅恨之情悠然而生,于是嗔问道:“你倒是回来不回来?叫人家成天价象在梦魂中一看,跟着那漫天的柳絮,绕世界去神游寻觅!”这种奇思遐想,意味深长,倾吐出少妇的无限离愁和情思。“魂梦逐杨花”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意境,对后代有所影响,如晏几道名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似受此词启发,又如章楶的《水龙吟·杨花》以及苏轼的和词,咏杨花而和思妇情怀相联,也似乎受到此词的影响。
《花间》词温庭筠多丽藻,韦庄多质朴语。顾敻成就不及温、韦,此词却能熔丽藻与质朴于一炉,使之疏密相间,恰到好处。
参考资料:
顾敻,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及字号均不详。前蜀王建通正(916)时,以小臣给事内廷,见秃鹫翔摩诃池上,作诗刺之,几遭不测之祸。后擢茂州刺史。入后蜀,累官至太尉。顾夐能诗善词。 《花间集》收其词55首,全部写男女艳情。
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相加。匪惟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呵。久为滞客,其意谓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盘。徒行负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宫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
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諐。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言辞既磬,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二子,与我连行。”
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飏于前,适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惊寤,以为风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为。蹴童子,呼曰:“吾为物所苦,亟起索烛照。”烛至,絺帷尽张。蚊数千,皆集帷旁,见烛乱散,如蚁如蝇,利嘴饫腹,充赤圆红。生骂童子曰:“此非吾血者耶?尔不谨,蹇帷而放之入。且彼异类也,防之苟至,乌能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已去矣。”
生乃拂席将寝,呼天而叹曰:“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
童子闻之,哑而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之间,二气絪緼,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驯之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为禽为兽,裸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栗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
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
素波笑浅流花,轻衫舞争飘霞,席上司空鬓华。酒阑歌罢,不知春在谁家? 别高宰
青山远远天台,白云隐隐萧台,回首江南倦客。西湖诗债,梅花等我归来。 春情
双双翠舞珠歌,卿卿酒病花魔,为问风流玉娥。海棠开过,牡丹消息如何? 渔父
忘形雨笠烟蓑,知心牧唱樵歌,明月清风共我。闲人三个,从他今古消磨。 秋江夜泊
斜阳万点昏鸦,西风两岸芦花,船系浔阳酒家。多情司马,青衫梦里琵琶。 题情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证候。甘心消受,谁教你会风流?
【混江龙】相思慰闷,绣屏斜倚正销魂。带围宽尽,消减精神。翠被任薰终
不暖,玉杯慵举几番温,鸾钗半鹑蝉鬓,长吁短叹,频啼痕。
【寄生草】琼簪折,宝鉴分。今春又惹前春恨,泪珠儿滴尽愁难尽,瘦庞儿
不似当时俊。思量几度甚时休,相思满腹何年尽?
【金盏儿】风逼透绣罗衾,风刮散楚台云。檐间铁马风敲韵,风摇闲阶翠竹
不堪闻。风筛帘影动,风传漏声频。风熏花气爽,风弄月华昏。
【后庭花】兽炉中香倦焚,银台上灯渐昏。罗帏里和衣睡,纱窗外曙色分。
想情人,起来时分,蹀金莲搓玉笋。
【赚煞】捱的到天明,却有谁亻秋问?咋夜和衣睡把罗裙皱损。一面残妆空
泪痕,日高也深院无人。掩重门,烦恼向谁论?独对菱花整乱云。恰待向瘦庞儿
上傅粉,欲梳妆却心困,气长吁呵的镜儿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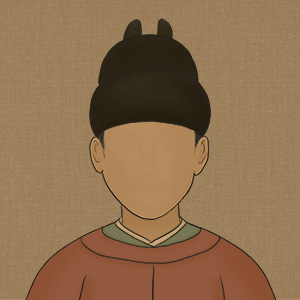 顾夐
顾夐 白居易
白居易 扬雄
扬雄 方孝孺
方孝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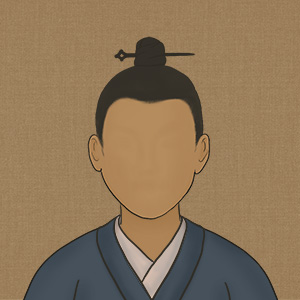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 贯云石
贯云石 韩元吉
韩元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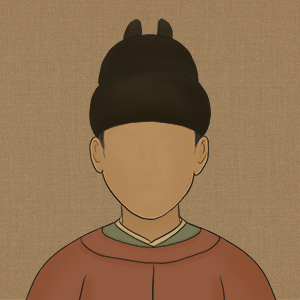 王衍
王衍 苏轼
苏轼 王质
王质 邹应龙
邹应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