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生在世,应知进退,用则行,不用则藏。不妨权且做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躬耕田园。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便可怡然自乐。
多年来就像孔子那样,辗转多地,南北驱驰,一意从政,而四处遭受挫折。还是学隐士长沮桀溺,隐居躬耕,不要学孔子四处奔波。
注释
踏莎行:词牌名,又名“喜朝天”“柳长春”“踏雪行”“平阳兴”“踏云行”“潇潇雨”等。双调小令,《张子野词》入“中吕宫”。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四言双起,例用对偶。
行藏用舍:语出《论语·述而》。
小人请学樊须稼:语出《论语·子路》。
长沮桀溺耦而耕:语出《论语·微子》。
丘何为是栖栖者:语出《论语·宪问》。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参考资料:
赏析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参考资料: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流水桃花鳜美,秋风莼菜鲈肥。不共时,皆佳味,几个人知?记得荆公旧日题:何处无鱼羹饭吃?羊续高高挂起,冯驩苦苦伤悲。大海边,长江内,多少渔矶?记得荆公旧日题:何处无鱼羹饭吃?鲲化鹏飞未必,鲤从龙去安知?漏网难,吞钩易,莫过前溪。记得荆公旧日题:何处无鱼羹饭吃?藏剑心肠利已,吞舟度量容谁?棹月归,邀云醉,缩项鳊肥。记得荆公旧日题:何处无鱼羹饭吃?
朱颜二十有四,正锦帏秋梦,玉帐春声。望吴江楚汉,明月伴英魂。浥浥小桥红浪湿,抚虚弦、何处得郎闻。雪堂老,千年一瞬,再击空明。
 辛弃疾
辛弃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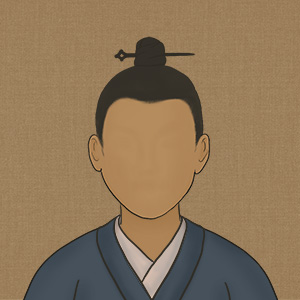 周德清
周德清 乔吉
乔吉 马致远
马致远 温庭筠
温庭筠 王质
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