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孟学士)要通过三峡前往巴陵的北边,(而有)经过天山到达弱水的东边。
有们所去的地方都有万里之遥,此次分别有俩都像飘蓬一样行踪不定。
自己西去像王粲避难荆州一样,孟学士北游像孔融赋闲在家一样。
往本回旋能听到鹤在夜里鸣叫,怅然若失地望着大雁秋来能带去信息。
分离的至亲还在家乡,有还在辛苦行走在关山要塞之中。
自己虽读书未获功名,但积极进取的志气并未泯灭。
注释
西使:出使西方。孟学士:即孟利贞。《旧书》本传:“受诏与少师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奏上之。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学士,指在学之士,学者。北北朝以后,以学士为司文学撰述之官。唐代翰林学士亦为文学侍从之臣。北游:游历江北。
地道:隘道,此当指长江三峡一带狭窄处。巴陵:郡名,唐改岳州为巴陵郡,治所在巴陵(今湖北岳阳市)。
天山:指横亘在今肃、青海一带的祁连山,匈奴人称天为祁连;唐时称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北)以北一带山脉为天山。弱水:古人称浅水或不流舟楫的河流为弱水,意为水弱不能胜舟;传说甚至有不胜芥或不胜鸿毛的。古籍所载弱水甚多,这里指西北绝远之处,即今青海一带。
万馀(yú)里:一万多里,极言其远,(指实有里数。馀,同“余”。
倚:倚靠。征蓬:蓬草,也叫飘蓬、飞莲,枯后根断遇风飞旋,用以比喻经常远行的人。
零雨:下雨。化用西晋泛人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泛》“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两句意。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北)人,东汉末文学家、泛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代指王勃。
清樽:清酒一杯。清,指酒。樽,酒器。孔融:字文举,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二十代孙,官至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故世称孔北海,东汉末年文学家、泛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以孔融比喻孟学士。
徘徊:往本回旋的样子。夜鹤:鹤夜里鸣叫。
怅:失意,懊恼。鸿:大雁,季候鸟,秋来冬去,有鸿雁传书之说。
骨肉:比喻至亲。胡秦外:指泛人家乡幽州范阳。胡,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少数名族的泛称。秦,古邑名,即秦城、秦亭,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秦代祖先(子始封于此,是秦的最早都邑。
风尘:指行旅,含有辛苦之意;也指污浊、纷扰的生活。这里的风尘指仕宦。关塞:关山要塞,指出入的要道。
唯:唯独,只有。剑锋:宝剑的锋刃,代指宝剑,这里指胸中抱负。
耿耿:光明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剑锋”的光芒。▲
赏析
此诗是初唐五言排律中的佼佼者,素来被诗论家所称道。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佺期:‘阊阖连云起,岩郎拂露开。’此类最为得体。”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评论说:“前人但赏其起语雄浑,须看一气承接,不平实,不板滞。后太白每有此种格法。”从这些评语里足以看出这首诗对当时诗坛和盛唐诗人的重要影响。
该诗是一篇感情真挚浓郁的友情诗。诗的前四句是说即将与友人离别,友人孟学士将要南下湖湘,此行可能经过狭窄陡峭的长江三峡,而自己则要西出塞外,与友人天各一方,相距万里之遥,故不胜悲伤。这几句笔力苍劲飞动,写得很有气势,特别是开头两句,场面开阔宏大。
“零雨悲王粲”一句中的王粲是东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代指王勃。唐人诗中用典,多喜用今人与前代名人同姓者比附,此即一例。这句是因王勃被贬斥而生悲伤借爱之情。“清樽别孔融”中的“孔融”是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这里当代指孟学士,以其才能、好客喜士与孔融相似而设喻。两句用典,一以姓同而比,一以事类,都很贴切身份。“徘徊”两句是设想之辞,说自亡与孟学土分别后将会彻夜不眠,望眼欲穿,等待大雁把信捎来。“骨肉”两句亦写别后情状,唯“胡秦外”与“关塞中”措语略嫌重复,只涉自己“西使”,而未切友人“南游”,但从通篇来看,不过是白璧微遐。
最后两句说剑锋耿耿,一则是比喻友人一腔正气,充沛天地。同时也暗示出自已“抱剑钦专”,“但令一顾重,不馁百身轻”(《刘生》),为国家荡平外寇、铲除奸佞的凌云壮志。
该诗送人而兼寓自已襟怀抱负,故题旨就比一般单纯写送别的诗深刻,特别是最后两句,使全篇陡然一振,豪情洋溢,托兴深远,就更非一般小儿女态临歧沾襟、凄楚伤感之作可比了。▲
创作背景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卢照邻奉命调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即将离开长安之时,适逢因编撰《瑶山玉彩》五百卷有功而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的友人孟利贞游江南,于是创作该诗赠予好友。
卢照邻,初唐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汉族,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其生卒年史无明载,卢照邻望族出身,曾为王府典签,又出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在文学上,他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号为“初唐四杰”。有7卷本的《卢升之集》、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存世。卢照邻尤工诗歌骈文,以歌行体为佳,不少佳句传颂不绝,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更被后人誉为经典。
【混江龙】庾楼高望,桂华初上海涯东。秋光于宙,夜色帘栊。谁使银蟾吞
暮霞,放教玉兔步睛空。人多在,管弦声里,诗酒乡中。
【六幺遍】烂银盘涌,冰轮动。辗玻璃万顷,无辙无踪。今宵最好,来夜怎
同。留恋孀娥相陪奉,天公,莫教清影转梧桐。
【后庭花】直须胜赏,想人生如转蓬。此夕休虚废,幽欢不易逢。快吟胸,
虹吞鲸吸,长川流不供。
【赚煞】听江楼,笛三弄,一曲悠然未终。裂石凌空声留亮,似波心夜
吼苍龙。唱道醉里诗成,谁为击金陵半夜钟,我今欲从嫦娥归去,盼青鸾飞上广
寒宫。 咏梅
所欠唯何?半生辜负,梅花债。洛京春色,直抵千金买。
【混江龙】水南佳会,主人樽俎胜安排。北州远客,西洛英才。和气须知席
上生,孤芳先向腊前开。宜珍赏,应题赋景,落笔书怀。
【六幺遍】故人应与,梅同态。梅虽雅淡,人更清白。人之风彩,梅之调格。
人与梅花俱可爱,无奈,岁寒姿可惜在尘埃。
【赚煞】惜花心,今番煞,恨不到调羹鼎鼐。此日梅花溪上客,胜当年刘阮
天台。劝酒留情,故意地教人强艳侧。酒休剩饮,花须少戴,也教人道洛阳来。
 卢照邻
卢照邻 王翱
王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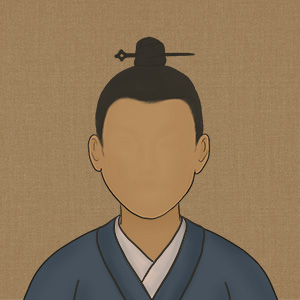 朱庭玉
朱庭玉 孙光宪
孙光宪 杨缵
杨缵 牛峤
牛峤 张煌言
张煌言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周邦彦
周邦彦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