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你看那花花树树交枝接叶,像是互诉着情愫;鸟儿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幅折枝画图。湖里的游鱼成双结对,在水下快乐地追逐;岸上的人家门当户对,男男女女都是亲密相处。一步步镶金铺翠,到处见琳琅满目。真是人间的天堂乐土。你可别糊里糊涂,把西湖当了卖了,白白地辜负。
注释
折枝:国画花卉画法的一种,指弃根干而单绘上部的花叶,形同折枝,故名。
厢:通“镶”。
赏析
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刘时中 [元] (约元成宗大德年间前后在世),洪都(今江西南昌)人,元代散曲家。生卒年、生平、字号均不详,约元成宗大德年间前后在世。官学士,时中工作曲,今存小令六十余支,套数三四首,以水仙子西湖四时渔歌最著名。
 刘时中
刘时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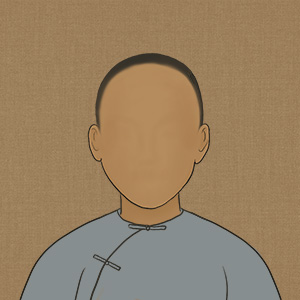 司马光 撰
司马光 撰 刘向
刘向 张可久
张可久 汪莘
汪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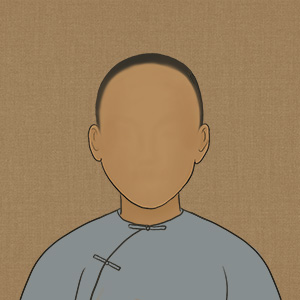 佟世南
佟世南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辛弃疾
辛弃疾 白居易
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