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这里是六个王朝的国都,三吴中秀丽的京城。
贤人就应委以重任,天子也要借助你的高名。
汪洋大海宁静了一边,长江万里得到了澄清。
你也许还须救赵良策,不要遗弃我这个侯嬴。
注释
升州:唐州名,乾元元年(758)改江宁郡置,上元二年(761)废,治所在今江苏南京。王忠臣:事迹不详。使君:即刺史。
六代:指吴、晋、宋、齐、梁、陈,六朝均建都金陵。国:此指天子之所都。
三吴:《水经注》以吴郡(今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三吴。《元和郡县志》则以吴郡、吴兴、丹阳(今江苏镇江)为三吴。说法不一。
重寄:重大的托付,犹重任。
巨海:大海。
“长江”句:当指平定刘展叛乱事。
应须:应当,应该。
侯嬴:战国时魏国隐士。年七十,家贫,为天梁夷门监者。信陵君引为门客。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秦军围赵都邯郸,魏王使晋鄙率军救晋。鄙畏秦,屯兵于邺以观望之。侯嬴向信陵君献计,并荐力士朱亥。信陵君至邺,使朱亥击杀晋鄙,窃得兵符夺其兵权,遂解邯郸之围。事见《史记·魏公子列传》。此处李白以侯嬴自比。
参考资料:
赏析
这首诗的首联,入手擒题,盛赞昇州。上句从纵的时间方面着眼,说这里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故都,让读者想见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下句从横的空间方面落笔,说这里是“三吴”地区的一座美丽的城市,让读者想见其江山多娇,物华天宝。丹阳郡为三国时吴所移置,治建业,故址在今南京市东南,亦即在诗人李白写此诗时的昇州。上下两句,一纵一横,气势宏伟,含盖多广。虽然这一联本于谢朓《入朝曲》的“江南佳丽地,六代帝王州”,但颠倒句序,使其落脚点在地更突出,而改“江南”为“三吴”,改“地”为“城”,改“州”为“国”,则有更工整、更确切的效应。如此为我所用,青胜于蓝,实非因袭陈言者可望其项背。
地灵则人杰,因此颔联紧承首联而颂王忠臣其人。上句说他人贤,帝王理当委托以重任;下句说他名高,天子凭借之以守此要地。这一联,似乎还巧妙地暗藏了被称颂者的姓名。上句,没有明说谁对“贤人当寄重”,但很明显指的应当为“王”。这“王”正是被称颂者的姓。下句、主语、谓语和宾语齐全,结构完整,但“天子”之所“借”以治国抚民的人,正是“忠臣”。这“忠臣”恰是被称颂者的“高名”。
昇州所辖,东极于海,西带长江,因此颈联放笔而涉及江海。上句的“一边静”,下句的“万里清”,从字面上看,写的是海与江的景象,实际上却说的是时局。这是针对这年正月,平定了刘展在这一带的作乱而言,又包含着诗人对史思明势焰尚嚣张,北方仍未平静的极大关注。对被赠诗的王忠臣来说,是既祝颂他所辖地区出现的清平,又希望他能扩大视野,看到北方的动乱。紧扣诗句,这一联则可作这样的解释:虽然“长江万里清”了,但是“巨海”才只有“一边静”,而非全静。
尾联,用侯嬴向信陵君献策窃符救赵事,以“应须”、“未肯”这样的推度语气,自比侯嬴,表现想要为国效命,在平定北方叛乱中建立功勋的愿望,希获被赠诗的王忠臣的理解和支持。据《史记·信陵君列传》载,侯嬴本为魏国大梁夷门监者,后为信陵君上客。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国平原君夫人为信陵君姊,屡次送书信请求魏国相救。魏王初使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后又惧秦而命晋鄙停兵观望。信陵君竭力劝说魏王进军,魏王终不听从。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侯嬴向信陵君献策,让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卧室盗出晋鄙兵符,然后去夺晋鄙军;如晋鄙不听,则使力士朱亥椎杀之。信陵信听从其策,果得兵符,杀晋鄙,率其兵而击秦军,救邯郸而存赵国。侯嬴与信陵君分别后,自刎而死。诗人李白这一想要为国效命,在平定北方的叛乱中建立功勋的愿望,在同一年所写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表现得更加明白。除诗题的表述外,诗中还说:“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可以与这尾联相互印证。遗憾的是诗人李白的这一愿望,无人理睬,使他终于在次年贫病交加而死。
李白是个充满豪情逸兴的诗人,不肯多写格律谨严的律诗,但偶有所作,皆为上品。这首五律,便可作证。它不死守五律定式声调,但平仄谐调。它以“城”、“名”、“清”和“嬴”四字押脚韵,皆属八庚,稳妥悠扬。它中间两联的对仗,两两相称,自然工整。首联亦对,更属难能。它紧紧抓住题目,以赞其地起,以颂其人承,以言时局转,以抒心曲收,层次清晰,中心突出。它始称“六代”,来引“侯嬴”,中言现在,上下千年,包举的时间漫长,运用“三吴”、“巨海”、“长江”、“万里”等意象,囊括的地域宽广,从而形成了阔大的意境,使人胸胆开张。它为赠昇州的王忠臣而作,却不限于一地,不囿于应酬,而能放眼全国,抒写壮怀。这首诗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受到后人的高度称赞。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参考资料: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为醉时写就,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第一折
(冲末净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孙,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都是狗养的。自家李存信的便是。这个是康君立。俺两个不会开弓蹬弩,亦不会厮杀相持;哥哥会唱,我便能舞。俺父亲是李克用,阿妈喜欢俺两个,无俺两个呵,酒也不吃,肉也不吃。若见俺两个呵,便吃酒肉。好生的爱俺两个!自破黄巢之后,太平无事,阿妈复夺的城池地面,着俺五百义儿家将,各处镇守。阿妈的言语:将邢州与俺两个镇守。那里是朱温家后门,他与俺父亲两个不和;他知俺在邢州镇守,他和俺相持厮杀。俺两个武艺不会,则会吃酒肉。倘或着他拿将去了,杀坏了俺两个怎了?(康君立云)如今阿妈将潞州天党郡与存孝镇守,潞州地面吃好酒好肉去。如今我和你两个,安排酒席,则说辞别阿妈,灌的阿妈醉了,咱两个便说:"邢州是朱温家后门,他与阿妈不和,倘若索战,俺两个死不打紧,着人知道呵,不坏了阿妈的名声!着李存孝镇守邢州去,可不好么?"(李存信云)俺两个则今日安排酒席,辞别父亲去走一遭来。我是李存信,他是康君立;两个真油嘴,实然是一对。(同下)(李克用同刘夫人领番卒子上)(李克用云)番、番、番,地恶人奔,骑宝马,生雕鞍。飞鹰走犬,野水荒山。渴饮羊酥酒,饥餐鹿脯干。凤翎箭手中施展,宝雕弓臂上斜弯。林间酒阑胡旋舞呵,着丹青写入画图间。某乃李克用是也。某袭封豳州节度使,因带酒打了段文楚,贬某在沙陀地面,已经十年。因黄巢作乱,奉圣人的命,加某为忻、代、石、岚都招讨使,破黄巢天下兵马大元帅。自离了沙陀,不数日之间,到此压关楼前,聚齐二十四处节度使,取胜长安。被吾儿存孝擒拿了邓天王,活挟了孟截海,挝打了张归霸;十八骑误入长安,大破黄巢,复夺了长安。圣人的命:犒劳某手下义儿家将,但是复夺的城池,着某手下义儿家将去各处镇守,防备盗贼。今日太平无事,四海晏然,正好与夫人众将饮酒快乐。小校安排下酒肴,可怎生不见周德威来?(周德威上,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列英豪。三军报罢平安喏,紧卷旗幡不动摇。某姓周,名德威,字镇远,山后朔州人也。今从李克用共破黄巢,太平无事,某为番汉都总管。今日元帅有请,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报复去,道有周德威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的元帅得知:有周德威在于门首。(李克用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周德
威云)元帅,周德威来了也。(李克用云)将军,今日请你来不为别的,想存孝孩儿多有功劳,我许与了他潞州上党郡与存孝孩儿镇守,把邢州与李存信、康君立镇守去。怎生不见李存信、康君立来?(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阿妈心内想,忽然到跟前。哥哥你放心,我这一过去,见了阿妈说了呵,便着存孝往邢州去。(康君立云)兄弟,只要你小心用意者。(李存信云)阿妈、阿者,想当初一日,阿妈的言语,将潞州上党郡与俺两个镇守来;今日阿妈与了存孝,可着俺两个邢州去!(做悲科)(李克用云)孩儿存信,你做甚么哭?(李存信云)阿妈,俺两个也早起晚夕,舞者唱者,扶持阿妈欢喜,怎下的着您两个孩儿往邢州去?(康君立云)阿妈,想邢州是朱温的后门,他与阿妈不和。倘若索战,俺两个不会甚么武艺。倘若拿将俺两个去了,俺两个死不打紧,阿妈吃起酒来,寻俺两个舞的唱的不在眼面前,阿妈不想成病!那其间生药铺里赎也赎不将俺两个来!(李存信云)阿妈,怎生可怜见着俺两个去潞州去,把邢州与存孝两口儿镇守罢,可也好?(李存信把盏科,云)哥哥,将酒来与阿妈把一盏。(李克用云)好两个孝顺的孩儿!我着你潞州上党郡去呵便了也。(康君立云)既是这等,谢了阿妈者!(周德威云)他两个有甚么功劳,把他潞州上党郡去!想飞虎将军南征北讨,东荡西除,困来马上眠,渴饮刀头血,他可以潞州去;他两个去不的!(李克用云)周将军说的是。小校,与我唤将存孝两口儿过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旦同李存孝云)(李存孝云)岩前打虎雄心在,勇敢当先敌兵败。上阵全凭铁飞挝,扶立乾坤唐世界。某本姓安,名敬思,雁门关飞虎峪灵丘县人氏。幼小父母双亡,多亏邓大户家中抚养成人,长大我就与他家牧羊。有阿妈李克用见某有打虎之力,招安我做义儿家将,封我做十三太保飞虎将军李存孝,就着我与邓大户家为婿。自从跟着阿妈,十八骑误入长安,大破黄巢,天下太平无事。圣人的命:将俺义儿家将复夺的城池,着俺各处镇守。阿妈的言语:着俺两口儿去潞州上党郡镇守。今有阿妈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道去。可早来到此也。夫人,我和你休过去;你看阿妈、阿者:大吹大擂,敲牛宰马,烹炮美味,五百番部落胡儿胡女扶持着,是好受用也。(正旦云)存孝,今日父亲饮宴,唤俺两口儿,俺见阿妈、阿者去。听了这乐韵悠扬,常好是受用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则听的乐动声齐,他是那大唐苗裔,排亲戚。今日俺父母相随,可正是龙虎风云会。
【混江龙】则俺这沙陀雄势,便有那珠围翠绕不稀奇。置造下珍羞百味,又不比水酒三杯。每日则是炮凤烹龙真受用,那一日不宰羊杀马做筵席!把那些个义儿家将都成立,一个个请官受赏,他每都荫子封妻。
(正旦云)存孝,我和你未过去,先望阿妈咱,可早醉了也。(李存孝云)咱不过去,见阿者、阿妈身上瀽的那酒呵,你见两边厢扶持着呵,十分的醉了也。(正旦唱)
【油葫芦】我见他执盏擎壶忙跪膝,他那里撒滞殢。阿妈那锦袍上全不顾酒淋漓,可正是他不择不拣干干的吃,他那里刚扶刚策醺醺的醉。一壁厢动乐器是大体,将一面鼍皮画鼓冬冬擂,悠悠的慢品鹧鸪笛。
【天下乐】你觑!兀那大小的儿郎列的整齐,端的是虚也波实,享富贵。我则见旁边厢坐着周德威,一壁厢摆着品肴,番官每紧紧随;我则见军排在两下里。
(正旦云)咱过去见阿妈去来。(李存孝云)咱过去来。(做见科)(李存孝云)阿妈,您孩儿存孝两口儿来了也。(李克用云)存孝孩儿来了。别的孩儿每各处镇守去了;今日吉日良辰,你两口儿便往邢州镇守去;康君立、李存信,你两个孩儿往潞州上党郡镇守去。(李存孝云)阿妈,当日未破黄巢时,阿妈的言语:"若你破了黄巢,天下太平,与你潞州上党郡镇守。"阿妈失其前言!今日阿妈着你孩儿镇守邢州,那邢州是朱温家后门,终日与他相持,可怎了也!(正旦云)存孝,我阿者行再告一告去。阿者,与存孝再说一声咱!(刘夫人云)孩儿,你去邢州镇守,阿妈醉了也,你且去咱。(李存孝云)阿者,当日与俺潞州上党郡,如今信着康君立、李存信,着俺去邢州去。阿者,怎生阿妈行再说一声,可也好也?(刘夫人云)你阿妈醉了也。(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你有甚么功劳,倒去潞州上党郡镇守去?(李存信云)阿妈的言语,着你邢州去;都是一般好地面,谁和你论甚么功劳!(李存孝云)想当日在压关楼前,觑三层排栅,七层围子,千员猛将,八卦阵图,那其间如踏平地也。(正旦云)咱阿妈好失信也!(唱)
【节节高】今日可便太平无事,全不想那用人的这之际。存孝与你安邦定国,他也曾恶征战图名图利。他觑的三层鹿角,七层围子,如登平地;端的是八卦阵图,千员骁将,施谋用计。阿者,他保护着唐朝社稷!
(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你两个有甚么功劳,倒去潞州镇守去也?(正里唱)
【元和令】端的是人不曾去铁衣,马不曾
摘鞍辔;则是着阿者今日向父亲行提:想着他从前出力气。可怎生的无功劳,倒与他一座好城池?阿者,则俺这李存孝图个甚的!
(刘夫人云)孩儿也,你阿妈醉了也,等他酒醒时再说。(正旦云)想康君主、李存信他有甚么功劳也!(唱)
【游四门】你则会饮酒食,着别人苦战敌。可不道生受了有谁知?阿妈,你则是抬举着李存信、康君立;他横枪纵马怎相持?你把他亏,人面逐高低。(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想当日十八骑误入长安,杀败葛从周,攻破黄巢,天下太平,是我的功劳;你有甚么功劳也?(李存信云)俺两个虽无功劳,俺两个可会唱会舞也哩。(正旦唱)
【胜葫芦】他几时得鞭敲金镫笑微微,人唱着凯歌回?遥望见军中磨绣旗,则你那滴羞蹀躞身体,迷留没乱心肺,唬的你劈留扑碌走如飞。
(李存孝云)你两个有甚么功劳?与你一匹劣马不会骑,与你一张硬弓不会射。则会吃酒肉,便是你的功劳也!(正旦唱)
【后庭花】与你一匹劣马不会骑,与你一张硬弓不会射。他比别人阵面上争功劳,你则会帐房里闲坐的。咱可便委其实,你便休得要瞒天瞒地。你饿时节挝肉吃,渴时节喝酪水,闲时节打髀殖,醉时节歪唱起,醉时节歪唱起。
【柳叶儿】你放下一十八般兵器,你轮不动那鞭、锏、挝、槌,您怎肯袒下臂膊刀厮劈?闹吵吵三军内,但听的马频嘶,早唬的悠悠荡荡魄散魂飞。(正旦云)存孝,则今日好日辰,收拾驮马辎重,辞别了阿妈、阿者,便索长行。(李存孝云)今日好日辰,辞别了阿妈、阿者,便索长行也。(正旦唱)
【尾声】罢、罢、罢,你可便难倚弟兄心,我今日不可公婆意。(刘夫人云)孩儿,你且休要性急,待你阿妈酒醒呵,再做商议。(正旦云)去则便了也。(唱)别近谤俺夫妻每甚的,只不过发尽儿掏窝不姓李,则今日暗昧神祗。(带云)惭愧也!(唱)势得一个远相离,各霸着城池;不恁的呵,这李存信、康君立断送了你。这一个个瞒心昧己,一个个献勤卖力,存孝,这两个巧舌头奸狡赖功贼!(下)
(刘夫人云)康君立、李存信,你阿妈醉了也,我且扶着回后堂中去也。(下)(周德威云)想着存孝破了黄巢,复夺取大唐天下,他的好地面与了这两个,可将邢州与了存孝。元帅今日醉了也,待明日酒醒,我自有话说。还着存孝两口儿潞州上党郡去,方称我之愿也!元帅殢酒负存孝,明石须论是与非。(下)(李存信云)康君立,如何?我说咱必然得潞州,今日果应其心。若是到潞州的丰富地面,不强似去邢州与朱温家每日交战?(康君立云)兄弟,想存孝这一去,必然有些见怪。等俺到的潞州,别寻取存孝一桩事,调唆阿妈杀坏了存孝,方称我平生之愿。则今日收拾行装,先往邢州,诈传着阿妈言语:着义儿家将各自认姓。他若认了本姓,咱搬唆阿妈杀了存孝,方称我平生之愿也。阿妈好吃酒,醉了似烧蒜。害杀安敬思,称俺平生愿。(同下)
第二折
(李存孝领番卒子上,云)铁铠辉光紧束身,虎皮妆就锦袍新。临军决胜声名大,永镇邢州保万民。某乃十三太保李存孝是也。官封为前部先锋、破黄巢都总管、金吾上将军。自到邢州为理,操练军卒有法,抚安百姓无私;杀王彦章,不敢正眼视之;镇朱全忠,不敢侵扰其境。今日无甚事,在此州衙闲坐,看有甚么人来。(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自离上党郡,不觉到邢州。自家李存信,这个是康君立。可早来到也。这个衙门就是邢州。小校报复去,道有李存信、康君立在于门首。(卒子云)理会的。(做报科,云)报的将军得知:有李存信、康君立来了也。(李存孝云)两个哥哥来了,必有阿妈的将令。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做见科)(康君立云)李存孝,阿妈将令:为你多有功劳,怕失迷了你本姓,着你出姓,还叫做安敬思。你惹不依着阿妈言语,要杀坏了你哩!你快着的改姓,我就要回阿妈的话去也。(李存孝云)怎生着我改了名姓?阿妈将令,不敢有违。小校,安排酒肴,二位哥哥吃了筵席去。(康君立云)不必吃筵席,俺回阿妈话去也。诈传着阿妈将令,着存孝更名改姓。调唆的父亲生嗔,耍了头也是干净。(同下)(李存孝云)阿妈,你孩儿多亏了阿妈抬举成人,封妻荫子;今日怎生着我改了姓?阿妈,我也曾苦征恶战,眠霜卧雪,多有功勋;今日不用着我了也!逐朝每日醉醺醺,信着谗言坏好人。我本是安邦定国李存孝,今日个太平不用旧将军。(下)(李克用同刘夫人上)(李克用云)喜遇太平无事日,正好开筵列绮罗。某乃李克用是也。奉圣人的命,着俺义儿家将各处镇守。四海安宁,八方无事,正好饮酒作乐。看有甚么人来。(李存信同康君立上,云)阿妈,祸事也!(李克用云)你为甚么大惊小怪的也?(康君立云)有李存孝到邢州,他怨恨父亲不与他潞州,他改了姓--安敬思。他领着飞虎军要杀阿妈哩!怎生是好?(李存信云)杀了阿妈不打紧,我两个怎生是好?我那阿妈也!(李克用云)颇奈存孝无礼,你改了姓便罢,怎生领飞虎军来杀我?更待干休!罢,则今日就点番兵,擒拿牧羊子走一遭去。(刘夫人云)住者!元帅,你怎么不寻思?李存孝孩儿他不是这等人。元帅,你且放心,我自往邢州去,若是存孝不曾改了姓呵,我自有个主意;他若改了姓呵,发兵擒拿,未为晚矣。也不用刀斧手扬威耀武,鸦脚枪齐摆军校。用机谋说转心回,两只手交付与一个存孝。(下)(李克用云)康君立、李存信,你阿者去了也;倘若存孝变了心肠,某亲拿这牧羊子走一遭去。说与俺能争
好斗的番官,舍生忘死的家将:一个个顶盔擐甲,一个个押箭弯弓,齐臻臻摆列剑戟,密匝匝搠立枪刀;三千鸦兵为先锋--逢山开道,遇水叠桥。左哨三千番兵能征惯战,右哨三千番兵猛烈雄骁,合后三千番兵推粮运草;更有俺五百义儿家将,都要的奋勇当先,相持对垒。坐下马似北海的毒蛟,鞍上将如南山的猛虎。某驱兵领将到邢州,亲捉忘恩牧羊子。家将英雄武艺全,番官猛烈敢当先。拿住存孝亲杀坏,血溅东南半壁天!(同下)(李存孝同正旦、卒子上)(李存孝云)欢喜未尽,烦恼到来。夫人不知,如今阿妈的言语,着康君立、李存信传说,但是五百义儿家将,着更改姓,休教我姓李,我不免改了安敬思。我想来阿妈信着这两个的言语呵,怎了也?(正旦云)将军,你休要信这两个的贼说!则怕你中他的计策,你也要寻思咱。(李存孝云)他两个亲来传说,教我改姓,非是我敢要改姓也。(正旦云)既然父亲教你改姓,则要你治国以忠,教民以义。(唱)
【南吕】【一枝花】常言道"官清民自安,法正天心顺",他那里"家贫显孝子",俺可便各自立功勋。无正事尊亲,着俺把各自姓排头儿问,则俺这叫爹娘的无气忿。今日个嫌俺辱没你家门,当初你将俺真心厮认。
(李存孝云)夫人,想当日破黄巢时,招安我做义儿家将;那其间不用我,可不好来!(正旦唱)
【梁州】又不曾相趁着狂朋怪友,又不曾关节做九眷十亲。俺破黄巢血战到三千阵,经了些十生九死,万苦千辛。俺出身入仕,荫子封妻,大人家踏地知根,前后军捺裤摩裩。俺、俺、俺,投至得画堂中列鼎重裀,是、是、是,投至向衙院里束杖理民,呀、呀、呀,俺可经了些个杀场上恶哏哏捉将擒人。畅好是不依本分!俺这里忠言不信,他则把谗言信;俺割股的倒做了生分,杀爹娘的无徒说他孝顺:不辨清浑!
(李存孝云)夫人,我在此闷坐。小校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孛老儿同小末尼上)(孛老儿云)老汉李大户。当日个我无儿,认义了这个小的做儿来;如今治下田产物业、庄宅农具,我如今有了亲儿了也,我不要你做儿,你出去!(小末尼云)父亲,当日你无儿,我与你做儿来;你如今有了田产物业、庄宅农具,你就不要我了!明有清官在,我和你去告来。可早来到衙门首也。冤屈也!(李存孝云)是甚么人在这门前大惊小怪的?小校,与我拿将过来者!(卒子做拿过科,云)理会的。已拿当面。(孛老儿同小末尼跪科)(李存孝云)兀的小人,你告甚么?(小末尼云)大人可怜见!当日我父亲无儿,要小人与他做儿;他如今有了田产物业、庄宅农具,他如今有了亲儿,不要我做儿子了,就要赶我出去,小人特来告。大人可怜见,与我做主也!(李存孝云)这小的和我则一般:当日用着他时便做儿,今日有了儿就不要他做儿。小校,将那老子与我打着者!(正旦云)你且休打,住者!(唱)
【牧羊关】听说罢心怀着闷,他可便无事哏,更打着这入衙来不问讳的乔民。则他这爷共儿常是相争,更和这子父每常时厮论。(李存孝云)小校,与我打着者!(正旦唱)词未尽将他来骂,口未落便拳敦,畅好背晦也萧丞相。(正旦云)赤瓦不刺嗨!(唱)你畅好是莽撞也祗候人。
(李存孝云)小校,与我打将出去!(卒子云)理会的。出去!(孛老儿云)我干着他打了我一顿,别处告诉去来。(同下)(刘夫人上,云)老身沙陀李克用之妻刘夫人是也。因为李存孝改了姓名,不数日到这邢州;问人来,果然改了姓,是安敬思。这里是李存孝宅中。左右报复去,道有阿者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的将军得知:有阿者来了也。(正旦云)你接阿者去,我换衣服去也。(做换服科)(刘夫人做见科)(李存孝云)早知阿者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做拜科)(刘夫人怒科,云)李存孝,阿妈怎生亏负你来?你就改了姓名,你好生无礼也!(李存孝云)阿者且息怒。小校,安排酒果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李存孝递酒科,云)阿者满饮一杯!(刘夫人云)孩儿,我不用酒。(正旦云)我且不过去,我这里望咱。阿者有些烦恼,可是为何也?(唱)
【红芍药】见阿者一头下马入宅门,慢慢的行过阶痕;见存孝擎壶把盏两三巡,他可也并不曾沾唇。我则见他迎头里嗔忿忿,全不肯息怒停嗔。我这里旁边侧立索殷勤,怎敢道怠慢因循!
【菩萨梁州】我这里便施礼数罢平身,抄着手儿前进。您这歹孩儿动问,阿者,你便远路风尘!(刘夫人云)休怪波,安敬思夫人!(正旦唱)听言罢着我去了三魂,可知道阿者便怀愁忿。这公事何须的问,何消的再写本!"到岸方知水隔村",细说原因。(刘夫人云)孩儿,俺两口儿怎生亏负着你来?你改了名姓!若不是康君立、李存信说呵,你阿妈不得知。如今你阿妈便要领大小番兵来擒拿你。我实不信,亲自到来,你果然改了姓名!俺怎生亏负你来也?(正旦云)存孝,你不说待怎么?(李存孝云)阿者,是康君立、李存信的言语,着俺五百义儿家将都改了姓,着您孩儿姓安。想您孩儿多亏着阿妈、阿者抬举的成人,封妻荫子,偌大的官职,怎敢忘了阿者、阿妈的思义!(做哭科,云)不由人嚎咷痛哭,提起来刀搅肺腑。抬举的立身扬名,阿者,怎忘你养身父母!(刘夫人云)我道孩儿无这等勾当,你阿妈好生的怪着的你!(正旦唱)
【骂玉郎】当初你腰间挂了先锋印,俺可也须当索受辛勤。他将那英雄慷慨施逞尽,他则是开绣旗,聚战马,冲军阵。
【感皇恩】阿者,他与你建立功勋,扶立乾坤;他与你破了黄巢,敌了归霸,败了朱温。那其间便招贤纳士,今日个俺可便偃武修文。到如今无了征战,绝了士马,罢了边尘。
【采茶歌】你怎生便将人不瞅问?怎生来太平不用俺旧将军?半纸功名百战身,转头高冢卧麒麟。(刘夫人云)媳妇儿,你在家中;我和孩儿两个见你阿妈,白那两个丑生的谎去来!(正旦云)阿者休着存孝去;到那里有康君立、李存信,枉送了存孝的性命也!(刘夫人云)孩儿,你放心!这句话到头来要个归着,要个下落处。孩儿,你在家中,我领存孝去,则有个主意也。(李存孝云)我这一去别辩个虚实,邓夫人放心也!(正旦唱)
【尾声】到那里着俺这刘夫人扑散了心头闷;不恁的呵!着俺这李父亲怎消磨了腹内嗔!别辩个假共真,全凭着这福神,并除了那祸根。你把那康君立、李存信,用着你那打大虫的拳头着一顿!想着那厮坑人来陷人,直打的那厮心肯意肯,可与你那争潞州冤仇证了本。(下)
(刘夫人云)孩儿收拾行装,你跟着我见你父亲去来。万丈水深须见底,止有人心难忖量。(同下)(李克用同李存信、康君立上)(李克用云)李存信、康君立,自从你阿者去之后,不知虚实,将酒来我吃。则怕存孝无有此事么?(李存信云)阿妈,他改了姓也,我怎敢说谎?(康君立云)我两个若是说谎了呵,大风里敢吹了我帽儿!(李克用云)此是实。将酒来,与我吃几杯。(康君立云)正好饮几杯。(刘夫人同李存孝上)(刘夫人云)孩儿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阿者来了也。(李克用云)阿者来了,请过来饮几杯。(卒子云)理会的。有请!(李存孝云)阿者先过去,替你孩儿说一声咱。(刘夫人云)孩儿,你放心,我知道。(刘夫人见科,云)李克用,你又醉了也!不是我去呵,险些儿送了孩儿也!(李存信报科,云)阿者,亚子哥哥打围去,围场中落马也!(刘夫人慌科,云)似这般如之奈何?我索看我孩儿去。(存孝扯科,云)阿者,替您孩儿说一说!(刘夫人云)亚子孩儿打围去,在围场中落马,我去看了孩儿便来也。(李存孝云)阿者去了,阿妈带酒也,信着这两个的言语,送了您孩儿的性命也!(刘夫人云)存孝无分晓:亲儿落马撞杀了,亲娘如何不疼?可不道"肠里出来肠里热"?我也顾不得的,我看孩儿去也。(打推科,下)(李存孝哭科,云)阿者,亚子落马痛关情,子母牵肠割肚疼。忽然二事在心上,义儿亲子假和真。亚子终是亲骨肉,我是四海与他人。"肠里出来肠里热",阿者,亲的原来则是亲!(李存信把盏科,云)阿妈满饮一杯。(李克用醉科,云)我醉了也。(康君立云)阿妈,有存孝在于门首,他背义忘恩。(李克用云)我五裂蔑迭!(下)(李存信云)哥哥,阿妈道:五裂蔑迭,醉了也,怎生是了?阿妈明日酒醒呵,则说道:"你着我五裂了来。"(康君立云)兄弟说的是。若不杀了存孝,明日阿妈酒醒,阿者说了,咱两个也是个死。小校与我拿将存孝来者!(李存孝云)康君立、李存信,将俺那里去?(李存信云)阿妈的言语:为你背义忘恩,五车裂了你哩!(李存孝云)阿妈,你好哏也!我有甚么罪过?将我五裂了!我死不争,邓夫人在家中岂知我死也?两个兄弟来,安休休、薛阿滩,将我虎皮袍、虎磕脑、铁燕挝与邓夫人,就是见我一般也。(李存孝哭科,云)邓夫人也,今朝我命一身亡,眼见的去赴云阳。娇妻暗想身无主,夫妇恩情也断肠!我死后淡烟衰草相为伴,枯木荒坟作故乡。夫妻再要重相见,夫人也,除是南柯梦一场!(李存信云)兀那厮,你听者:用机谋仔?
第三折
(刘夫人上、云)描鸾刺绣不曾习,劣马弯弓敢战敌。围场队里能射虎,临军对阵兵机识。老身刘夫人是也。昨日引将存孝孩儿来阿妈行欲待说也,不想亚子在围场中落马,我亲到围场中看孩儿,原来不曾落马,都是李存信、康君立的智量。未知存孝孩儿怎生,使一个小番探听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旦扮莽古歹上,云)自家莽古歹便是。奉阿者的言语,着吾打探存孝去;不想阿妈醉了,信着康君立、李存信的言语,将存孝五裂了。不敢久停久住,回阿者的话走一遭去也。(唱)
【中吕】【粉蝶儿】颇奈这两个奸邪,看承做当职忠烈,想俺那无正事好酒的爹爹!他两个似虺蛇,如蝮蝎,心肠乖劣。我呸呸的走似风车,不付能盼到宅舍。
【醉春风】一托气走将来,两只脚不暂歇;从头-一对阿者,我这里便说、说。是做的泼水难收,至死也无对,今日个一桩也不借。
(刘夫人云)阿的好小番也!暖帽貂裘最堪宜,小番平步走如飞。吾儿存孝分诉罢,尽在来人是与非。你见了存孝,他阿妈醉了,康君立、李存信说甚么来?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旦唱)
【上小楼】则俺那阿妈醉也,心中乖劣;他两个巧语花言,鼓脑争头,损坏英杰。他两个厮间别,犯口舌,不教分说;他两个旁边相倚强作孽。(刘夫人云)小番,他阿妈说甚么来?存孝说甚么来?李阿妈醺醺酒殢,李存孝忠心仁义。子父每两意相投,犯唇舌存信、君立。他阿妈与存孝谁的是,谁的不是,再说一遍咱。(正旦唱)
【上小楼】做儿的会做儿,做爷的会做爷,子父每无一个差迟,生各札的义断恩绝!阿妈那里紧当者,紧拦者,不着疼热。他道是:"你这姓安的怎做李家枝叶!"
(刘夫人云)小番,阿妈那里有两逆贼么?(莽古歹云)是那两个?(刘夫人云)一个是康君立,双尾蝎侵入骨髓;一个是李存信,两头蛇谗言佞语。他则要损忠良英雄虎将,他全无那安邦计赤心报国。那两个怎生支吾来?(莽古歹云)阿者,听你孩儿从头至尾说与阿者,则是休烦恼也!(唱)
【十二月】则您那康君立哏绝,则您那李存信似蝎蜇;可端的凭着他劣缺,端的是今古皆绝。枉了他那眠霜卧雪,阿妈他水性随邪。
(刘夫人云)俺想存孝孩儿,华严川舍命,大破黄巢定边疆;他是那擎天白玉柱,端的是驾海紫金梁。他两个无徒,怎生害存孝来?(正旦唱)
【尧民歌】他把一条紫金梁生砍做两三截,阿者休波,是他便那里每分说!想着十八骑长安城内逞豪杰,今日个则落的足律律的旋风踅,我可便伤也波嗟。将存孝见时节,阿者,则除是水底下捞明月!(刘夫人云)小番,你要说来又不说,可是为甚么来?(莽古歹云)李存信、康君立的言语,将存孝五车裂死了也!(刘夫人云)苦死的儿也!(莽古歹云)他临死时,将存孝棍棒临身,毁骂了千言万语,眼见的命掩黄泉。(刘夫人云)存孝儿衔冤负屈,孩儿怎生死了来?(正旦唱)
【耍孩儿】则听的喝一声马下如雷烈,恰便似鹘打寒鸠哏绝。那两个快走向前来,那存孝待分说怎的分说?一个指着嘴缝连骂到有三十句,一个扶着软肋里扑扑扑的撞到五六靴。委实的难割舍,将存孝五车裂坏,霎时间七段八节。
(刘夫人云)想必那厮取存孝有罪招状,责日词无冤文书,知赚的推在法场,暗送了七尺身躯。(正旦唱)
【三煞】又不曾取罪名,又不曾点纸节;可是他前推后拥强牵拽。军兵铁桶周围闹,棍棒麻林前后遮,扑碌碌推到法场也。称了那两个贼汉的心愿,屈杀了一个英杰!
(刘夫人云)想当日俺那存孝孩儿多有功劳:活挟了孟截海,杀了邓天王,枪搠杀张归霸,十八骑入长安,挝打杀耿彪,火烧了永丰仓,有九牛之力,打虎之威。怎生死了我那孩儿来!(莽古歹云)存孝道:(唱)
【二煞】我也曾把一个邓天王来旗下斩,我也曾把孟截海马上挟,我也曾将大虫打的流鲜血,我也曾双挝打杀千员将。今日九牛力,挡不的五辆车五下里把身躯拽。将军死的苦痛,见了的那一个不伤嗟!(刘夫人云)五辆车,五五二十五头牛,一齐的拽,存孝怎生者?(正旦唱)
【尾声】打的那头口门惊惊跳跳;叫道是"打打俫俫"。则见那忽剌鞭飕飕的摔动一齐拽,将您那打虎的将军命送了也!(下)
(刘夫人云)李克用,你信着这两个贼子的言语,将俺存孝孩儿屈死了。李克用,你好哏也!五辆车五下齐拽,铁石人嚎咷痛哭。将身躯骨肉分开,血染赤黄沙地土。再不能子母团圆,越思量越添凄楚。刘夫人苦痛哀哉,李存孝身归地府。(做哭科,云)哎哟,存孝孩儿也,则被你痛杀我也!(下)
第四折
(李克用、李存信、康君立领番卒子上)(李克用云)塞上羌管韵,北风战马嘶。缕金画面鼓,云月皂雕旗。某乃李克用是也。昨朝与众番官饮酒,我十分带酒,说道存孝孩儿来了也。小番,与我唤存孝孩儿来者!(李存信云)如之奈何?(刘夫人上,云)李克用,你做的好勾当!信着两个丑生,每日饮酒,怎生将存孝孩儿五裂了?我亲到的邢州,并不曾改了名姓;都是康君立、李存信这两个贼丑生的见识,着他改做安敬思。昨日我领着存孝孩儿来见你,你怎生教那两个贼子五车裂了存孝?媳妇儿将着骨殖,背将邓家庄去了。孩儿也,兀的不痛杀我也!(李克用云)夫人,你不说我怎生知道!都是这两个送了我那孩儿也!我说道:"五裂蔑迭,我醉了也。"他怎生将孩儿五裂了!把这两个无徒拿到邓家庄上杀坏了,剖腹剜心,与俺孩儿报了冤仇也!便安排灵位祭物,便差人赶回媳妇儿来者。(做哭科,云)哎哟!存孝儿也!我听言说罢泪千行,过如刀搅我心肠。义儿家将都悲戚,只因带酒损忠良。颇奈存信康君立,五裂存孝一身亡。大小儿郎都挂孝,家将番官痛悲伤。哎!你个有仁有义忠孝子,休怨我无恩无义的老爹娘!(同下)(正旦拿引魂幡哭上,云)闪杀我也,存孝也!痛杀我也,存孝也!(唱)
【双调】【新水令】我将这引魂幡招飐到两三遭,存孝也,则你这一灵儿休忘了阳关大道。我扑籁籁泪似倾,急穰穰意如烧;我避不得水远山遥,须有一个日头走到。
【水仙子】我将这引魂幡执定在手中摇,我将这骨殖匣轻轻的自背着。则你这悠悠的魂魄儿无消耗,(带云)你这里不是飞虎峪那,(唱)你可休冥冥杳杳差去了!忍不住、忍不住痛哭嚎咷,一会儿赤留乞良气,一会儿家迷留没乱倒。天那,痛煞煞的心痒难挠!
(刘夫人上,云)兀的不是媳妇儿邓夫人!我试叫他一声咱:媳妇儿,邓夫人,你住者!(正旦唱)
【庆东原】踏踏的忙那步,呸呸的不住脚,是谁人吖吖的脑背后高声叫?(刘夫人云)邓夫人,是我也。(做见哭科,云)痛杀我也,存孝孩儿也!(正旦唱)阿者,你把我这存孝来送也!(刘夫人云)我说甚么来?(正旦唱)你可知道"不着落保,到头来须有个归着"。(刘夫人云)媳妇儿也,你不曾忘了一句儿也。(正旦唱)这烦恼我心知,待对着阿谁道?(刘夫人云)孩儿,你且放下骨殖匣儿,你阿妈将二贼子拿将来与存孝孩儿报仇雪恨也。(李克用同周德威领番卒子拿李存信、康君立上)(李克用云)媳妇儿也,你亦辞我一辞去,怕做甚么?将那祭祀的物件来,将虎磕脑、螭虎带、铁飞挝供养在存孝灵前,将康君立、李存信绳缠索绑祭祀了,慢慢的杀坏了这两个贼子。周将军与我读祭文咱。(周德威读祭文科)维大口口九月上旬日,忻、代、石、岚、雁门关都招讨使,破黄巢兵马大元帅李克用等,致祭于故男飞虎将军李存孝之灵曰:惟灵生居朔漠,长在飞虎,累遇敌战,猿臂善射。两张弓,两袋箭,左右能射之;手舞铁挝,斩将不及三合。曾打虎在山峪之中,破贼兵禁城之内、挝打死耿彪,立诛三将,杀坏五虎。击破一字长蛇阵,杀败葛从周。渭南三战,十八骑误入长安。箭射黄巨夭,恶战傅存审,力伏李罕之,活挟邓天王,病战高思继,生擒孟截海,大败王彦章。救黎民复入长安城,享太平再临京兆府。祭奠英灵,亲藩悔罪。今克用因殢酒听信狂言,故损坏义男家将。今将贼子尽该诛戮,与公雪冤。众将缟素,俺哭的那无情草木改色,青山天地无颜。将军阳世不将金印挂,阴司却掌鬼兵权。众将番官痛嚎咷,壁上飞挝血未消,阶下枉拴龙驹马,帐前空挂虎皮袍。英雄存孝今朝丧,多曾出力建功劳。赤心报国安天下,万古清风把姓标。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正旦唱)
【川拨棹】则听的父亲道,将孩儿屈送了。家将每痛哭嚎咷,想着盖世功劳,万载名标。都与他持服挂孝,众儿郎膝跪着。
【七兄弟】你兀的据着,枉了见功劳。沉默默两柄燕挝落,骨剌剌杂彩绣旗摇,扑冬冬画鼓征鼙操。
【梅花酒】你戴一顶虎磕脑,马跨着黄骠,箭插着钢凿,弓控着花梢。经了些地寒毡帐冷,杀气阵云高。我这里猛觑了,则被你痛杀我也李存孝!
【收江南】呀,可怎生帐前空挂着虎皮袍?枉了你忘生舍死立唐朝!枉了你横枪纵马过溪桥!兀的是下梢,枉了你一十八骑破黄巢!
(李克用云)小番,将李存信、康君立拿在灵前,与我杀坏了者!(番卒子做拿二净科,云)理会的。(李存信云)阿妈,怎生可怜见。饶了我两个罢!(康君立云)阿妈,若是饶我这一遭,下次再不敢了也!(正旦唱)
【沽美酒】康君立你自道,李存信祸来到。把存孝赚入法场屈送了,摔碎了我浑家大小,任究竟罪难逃。
【太平令】也是你争弱,拿住你该剐该敲!聚集的人员好闹,准备车马绳索,把这厮绑了,五车裂了,可与俺李存孝一还一报!
(李克用云)小番,将,贼子五裂了者!(番卒子做杀李存信、康君立科,云)理会的。(李存信云)我死也。(下)(李克用云)既然将二贼子五裂了,与我存孝孩儿报了冤仇,将孩儿墓顶上封官,邓夫人与你一座好城池养老。你听者:李存信妒能害贤,飞虎将负屈衔冤。邓夫人哀哉苦恸,为夫主遇难遭愆。康君立存信贼子,五车裂死在街前。设一个黄箓大醮,超度俺存孝生天。
奇兵破愁城酒盏,离情纟全恨锁眉山。沉水烧残,绣被熏兰,只是春寒。 山居
枕琴书睡足柴门,时有清风,为扫红尘。林鸟呼名,山猿逐妇,野兽窥人,
唤稚子涤壶洗樽,致邻僧贳酒论文。全我天真,休问白鱼,且醉白云。 读史
慨西风壮志阑珊,莫泣途穷,便可身闲。贾谊南迁,冯唐老去,关羽西还。
但愿生还玉关,不将剑斩楼兰。转首苍颜,好觅菟裘,休问天山。 秋景
秋声先到梧桐,挂雨雌霓,拂槛雄风。几点青山,一泓素月,满地丹枫。肠
缕断情欺醉容,漏声迟霜满愁红。长笛声中,罨画楼东,泪洒征鸿。
一半儿酒。 落花
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消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
一半儿雨。 春情
眉传雨恨母先疑,眼送云情人早知,口散风声谁唤起。这别离,一半儿因咱
一半儿你。
夺残造化功,占断繁华富,芳名喧上苑,和气满皇都。论春秀谁如,一任教浪蕊闲花坞。正是断人肠三月初,本待学煮海张生,生扭做游春杜甫。
【梁州】齐臻臻珠围翠绕,冷清清绿暗红疏,但合眼梦里寻春去。春光堪画,春景堪图,春心狂荡,春梦何如?消春愁不曾两叶眉舒,殢春娇一点心酥。感春情来来往往蜂媒,动春意哀哀怨怨杜宇,乱春心乔乔怯怯莺雏。春光,怎如?绿窗犹唱留春住,怎肯把春负?长要春风醉后扶,春梦似华胥。
【隔尾】休耽阁一天柳絮如绵舞,满地残花似锦铺,九十日春光等闲赠。云窗月户,狂风聚雨,休没乱杀东君做不得主。
 李白
李白 白居易
白居易 左丘明
左丘明 关汉卿
关汉卿 李致远
李致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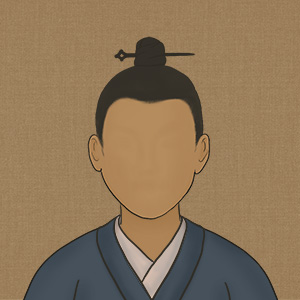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 马致远
马致远 赵昂
赵昂 严蕊
严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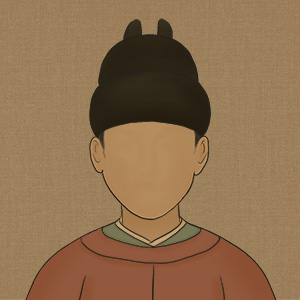 鹿虔扆
鹿虔扆 蔡伸
蔡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