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诗文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是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辆;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旁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
然吾闻杨侯之去,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肖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种带联地露,藕香玉井湫,曾向苕溪溪上游。愁,结花成并斗,何时又,共登仙叶舟。
观泉
靖节黄花径,子猷苍玉亭,千涧飞来六月冰。清,素琴无意听。阑干静,白云钟一声。
观猎
雪点苍鹰俊,玉花骢马骄,广利将军猎近郊。袍,织成金翠毛。随军乐,绣旗双皂雕。
也莫向竹边孤负雪。也莫向柳边孤负月。闲过了,总成痴。种花事业无人问,惜花情绪只天知。笑山中:云出早,鸟归迟。
 左丘明
左丘明 司马迁
司马迁 韩愈
韩愈 高启
高启 吴西逸
吴西逸 张可久
张可久 太学诸生
太学诸生 元好问
元好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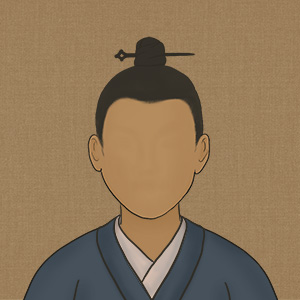 曹伯启
曹伯启 王庭筠
王庭筠 辛弃疾
辛弃疾 李煜
李煜 陈允平
陈允平 张抡
张抡 张元干
张元干 赵长卿
赵长卿